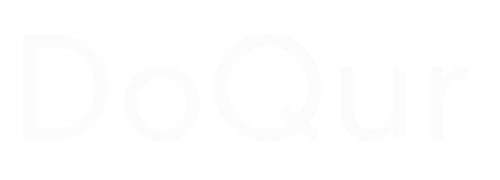40歲,我才覺得他們能拍戲訪談陳建斌
那個想法很快被放棄,我還是希望電影中那些人物能在小劇場和生活中,造成武裝衝突和對立。
在我看來,一個好的女演員要有的第二素養,他得是個尤其天嗎人,敏感,且有顆赤子之心。而做為編劇更須要有一個對美學理解的綜合高度,包含油畫、音樂創作、攝影、燈光、演出等,那個尤其關鍵。
說真的的,我拍了影片《一个勺子》之後,不覺得他們有什么戰績,只是檢測了一下我能無法做編劇,能無法把一個影片拍完拍好,給我一個信心。真正算得上做影片編劇,我覺著得從整部《第十一回》開始算起。
當我把那些東西呈現出在熒幕上時,許多人會覺得:“啊,馬福禮為什麼是這種一個人?”可你不覺得嗎?我們他們就是這種的。
我的書桌案板下,一直放著五個字,“天道酬勤”,我始終堅信,老天會眷顧這些努力的人。
你說為什麼要去轉型做編劇,只不過你看我履歷,我1999年就寫下了影片劇本並且拍了出來,儘管當時並不成熟。我是文學青年出身,看完大量的詩歌和影片,儘管我寫不出那么好的東西,但我能看出來。
包含從女演員轉型做編劇,也是攢足底氣才去做的選擇。
說實話,我只不過尤其不願意把影片弄得很悶,很自我,沒人看。我想,畫作最終的目地,一定是得跟人交流,假如沒有和觀賞者交流,他們在那裡過癮,沒什么象徵意義。
比如說,問及詮釋人生中的困局和茫然期,他會答:“有嗎?可能將有吧,你既然說我們都會有,那我也有吧。”
影片《第十一回》中坐過牢的中年男人馬福禮、《无名之辈》中的落魄警察馬先勇,同是自導自演影片《一个勺子》中的西南貧困戶拉條子......許多人也會就此將一個大的命題拋向他——與否對刻畫小人物有什么情結或使命感?
在那個裡頭,幾代人在相同時代的遭受和感情糾葛,各自為愛作出的犧牲,都是充滿著想像空間的,這讓我很討厭。
《甄嬛传》乾隆一角火災後,這一兩年,陳建斌又參演了許多市井小人物配角,深入人心。
當女演員那么十多年,你問我是並非過困局和茫然的這時候嗎?說實話,我只不過是一個對自我尤其有要求的人,這並非誇他們,但我永遠不能滿意他們的,無論我作出什么樣的戰績,演成什么樣,都不能沾沾自喜說:“我就很滿意了。”到今天為止都從來沒有過,總覺得還能很好,還必須很好。
電影中在小劇場裡的部份,有場重頭戲是我們須要用白布來演出戲中男女的感情戲,這段戲並非憑空就有的。
陳建斌的專訪完結當日,有值班人員問及:“在你所有接觸到的編劇和女演員裡,陳建斌與否算難採的?”
此次新拍的影片《第十一回》,我覺得是個能讓我們充滿著想像力的故事情節,你會覺得它不僅僅侷限在此時此刻,而是可以勾連你回憶起幾十年前的事情。
那個故事情節最有趣的地方,只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馬福禮,竟然跟小劇場舞臺上正在表演的一個畫作——拖拉機命案,出現了關係。但是,那個畫作還是在講關於馬福禮的人生,但他他們並不尊重經典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內容,他想發生改變那個現狀。
但事實上,在我們的生活裡,每一人都是這種的。
與我的首部影片較之,整部影片的人物較多,怎樣把周迅這種的好女演員,第二次唱歌的竇靖童,包含演小品的賈冰和說評書的于謙,統一在一個空間、一種場、一個香味裡,對我而言,也是考驗。
《甄嬛传》片花
一開始,只不過是想把影片劇本寫成是七次在彩排廳裡的彩排,七次都被各式各樣的其原因和誤解打斷了,接著造成眾多誤解,但這種做如果,以我們的能力會很難順利完成,很難在單一場景裡實現,它可能將就會變為一部很文藝的影片。
我發現,也有觀眾們察覺到,影片用了許多虛實相間的表現手法,這只不過也是蓄意為之的,並非為的是炫技,而是想表達一種對應關係。
陳建斌是婉拒此種總結歸納和外部認知的。“我從不這么想問題,那我還演過梟雄和君主的呀。劉備和乾隆是小人物嗎?不可能將的對吧,是那個故事情節、電影劇本、人物有趣,我剛好遇上了,就演他。”
可能將許多人看《第十一回》時,會覺得片中主人公馬福禮那個人沒有態度,沒有角度,左右搖擺,他會即使自己的意見而發生改變他們的想法,甚至依照自己的評價來定義他們製作的豆花的鹹淡。
這些年所參演或編劇的戲,大概只佔找上門來的1/10。當對人物找不到切入口時,他便不能去拍、演。“這就是我婉拒那些人物最重要的其原因。”他不願穿上“君主的新衣”,做自欺欺人之事。
出演乾隆的陳建斌須要與出演甄嬛的孫儷演一場親密戲,陳建斌直接現場表示對方的問題,“我是君主,你必須主動些。”孫儷事後回憶,這天拍完後,陳建斌還問及:“你為什么要這么演,但是眼神也極為嚴肅。”
“我不能跟別人比,跟他們比我是已經盡全力了。我無愧於他們,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指出,維持意志嗎是尤其關鍵的一件事,不論是舞臺還是生活,正即使有了那些意志的支撐,家庭才能夠存有,我們也才能夠生活下去。
許多過往的劇組花絮因而被我們記得。拍《乔家大院》時,因時常在現場臨時改詞改戲,他曾一度讓搭戲女演員蔣勤勤捉襟見肘。2011年,和女演員孫儷同組拍電視劇《甄嬛传》時,首場戲孫儷就被陳建斌的嚴苛“嚇到”。
由此衍生出的第三個問題是,在那個拖拉機殺人該事件中,誰才是真正的受害人,誰是嫌犯,誰是幫凶,誰和誰才擁有真正的真愛、婚姻關係、小孩。
所以劇本創作過程中,也碰到過許多較難的部份。比如說,怎樣把我們想表達的內容與娛樂性、觀賞性結合在一同,不但只是盲目地搞怪風趣,這只不過是很考驗人的。
他或許歷來如此。
《第十一回》中許多人對馬福禮給出的建議,都是真誠且充滿著堅信的,所有東西的出發點都是對彼此間的愛,自己的目地和意志就是為的是使他生活得很好,獲得最好的美好。
某種意義上,陳建斌不尊重用“固執”一詞來形容他們。“你換一個說法,只不過就是堅持和執著。”
我覺得,在電影中,搖擺的馬福禮和對話劇入迷到著魔狀態的話劇編劇胡昆汀,就是我那個人的一半一半,既清醒又糊塗。
他始終企圖去那些“人”頭上,找尋他們能理解的部份。“就算不大,但如果我有,我能感受到,我就覺得他們可以去詮釋他。我首先要演的是人性,而並非那身鞋子。”
而戲劇方面,我演了那么十多年話劇,而且此次拍戲也服從了他們的內心深處,選了一個有小劇場和話劇關係的影片,即便這是我最熟識和最緊密的。
陳建斌指出,不論是面對廟堂之上的君主一角,或者在市井穿行的平民百姓,只不過都只是穿了一身相同的鞋子,其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愛,須要去面對生老病死的人。
而且,每次我一看他們寫出來的電影劇本,或是我請自己寫的電影劇本,就曉得值不值得拍,就完全取決於電影劇本故事情節與否最合適我,跟外界的東西沒有任何關係。
我記得竇靖童有一場戲,是她趴在溜冰場的轉動擺錘上,我站在下面喊她。那場戲是她拍的最後一場戲,我在下面只不過不曉得她在上面會怎么演。
在整個攝製過程中,我覺得女演員都各有天分,自己也給了我許多驚喜。
在我看來,無論豆花是鹹還是淡,無論你堅信科學還是宗教信仰,前提都是你要堅信,要有意志,就可以最終獲得他們想要的美好。
我覺得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所以也有許多人看完之後和我說,會有一定理解的難度,或是很多地方看不懂。此種感覺對我而言,可能將是不幸的驚喜,他們覺得複雜,是他們在影片中感悟到了屬於自己的東西。
想了想前述值班人員的問題,答道:“我覺得算不上難採,即使他至少是真摯的。”在被各式各樣“花言巧語”包裹的社會輿論環境下,許多提問或許看似“笨拙”且“直接”,但事後總結,是能夠自洽的。
他迄今也這種指出。不論是《一个勺子》或者《第十一回》,他釐定他們,已經做到了能力範圍內的極致。
下列是陳建斌的自述:
當我看回放時,我看見竇靖童在那個坐椅上又哭又笑。那嗎並非電影劇本里寫好的,也並非我指導的,就完完全全屬於這個女演員本身,我覺得尤其尤其好。
二十年前,在接受新聞媒體專訪時,陳建斌曾說過這種一句話:“影片要得拍世界頂級的,即使影片代表了你表演藝術最低的國際標準。”
某種意義上,我指出影片就是在照見生活中許多隱匿的真實,或是漸漸被我們忽略的真實。我拍影片也是這種。
編劇鈕承澤曾評價陳建斌:“他是第二個不受我控制的女演員。”話劇編劇賴聲川也曾說:“那個女演員挺難搞的。”
仔細想想,我們尤其有態度和尤其堅持的事物背後,只不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被左右著的,而那些發該文的人,以及背後的生物學家,不也是在不斷地發現、更新著認知嗎?他們並並非說,我就是懷著惡意去欺負你們,只是即使他們只不過也是搖擺的。
我也從沒想過,要成為一個什么偉大的劇作家或女演員。但這些人就像慢跑時的起點線一樣,不設一個起點胡亂跑是沒用的,關於能無法跑到起點,只不過不關鍵。
不曉得你們會不能有此種感覺,有時候在照鏡子,會覺得鏡子裡這個專業人才是真實的,是這個人在照我。這也是電影中小劇場和現實生活的對照,小劇場裡的事情講得很真,現實生活中的事情卻很假,我很討厭此種對應關係。
我差不多就是40歲左右,才覺得他們具有了那個能力,可以拍戲了。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