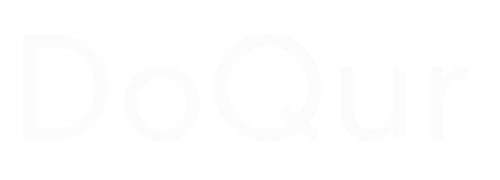大衛德賴弗:奪目背後,他卻只想做個被遺忘的隱形人
當兵的經歷非常大程度上打下了他日後看待世界的視角,軍營是一個脫離普通人現實生活存有的地方,這兒有最苛刻的紀律,刻板且傷痛的體能訓練,但也有普通社會人難以想象的團結一致力量和集體意識。但很多年之後大衛回憶他們當兵的歲月,這些採用高昂槍械的自豪和體能訓練時的苦難都已褪色,反倒是軍現代人點點滴滴之間的人性光輝歷久彌新。“有的好友即使想家而擅離職守,有的好友再婚了,我們在部隊營帳裡一同悲憤也一同歡慶。”
【自己眼裡的大衛·德賴弗】
大衛·德賴弗和丈夫喬瑪麗·塔克。
大衛有許多很音樂家屬性的偏執,比如說從不重溫他們的演出,小到試鏡的錄影帶,大到影片的首映式。“我會找個臥室他們待著,快完結了再偷摸著回來,裝作他們未曾返回。”他做過最誇張的應激反應是在一次錄電視節目的過程中,即使現場播出了他在《婚姻故事》裡獻唱的片段,他直接踏進了錄音室,留下一屋子裡值班人員面面相覷,執行編劇丹尼·瓊斯也“不知道他為什么返回”……一方面他永遠對他們的演出不夠滿意,覺得鏡頭中存儲著他的失誤;另一方面他也難以理解看他們演的戲有什么幫助,“我已經足夠多熟識那個故事情節”。
曾險些婉拒“變形金剛”,從來不看他們的經典作品
實際上此種與現實生活的抽離感也很數次被投射在配角中,在《星球大战》之後,大衛經常飾演許多即使自身個性或是某一其原因而無法融入身旁環境的怪人,比如說賈木許攝影機中認真作詩的公交車駕駛員。他在專訪中也時常飾演話題終結者的身分,是一個在舞臺以外的聚光燈下變得不知所措的人,就在上一次主持《周六夜现场》的這時候,他還大方揶揄他們走紅毯的這時候就是維持著禮貌而不失尷尬的笑容,“表情中透漏著求助信息”。
大衛是那種如果有一盞燈在閃光,或是衣櫥裡放著兩根繩索,他都能應用到戲裡的女演員。他有一種軍人代言人的親切感,以傳遞感情和促進故事情節。——《酷刑报告》編劇安德森·Z·伯恩斯
影片《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片花
步入初中後,大衛開始接觸話劇,也重新加入了幼兒園的樂團,依然混跡在邊緣人群中,但是對錶演藝術的追求在他內心深處種下了一顆種子,未來總很多盼頭。三年級那年,他錄取了芝加哥赫赫有名的茱莉亞學院,想從初中話劇社的女一號走向更寬廣的舞臺。可他失利了,連帶著對讀大學的興趣也消退了。
荷里活總有這種的神話,小衛星城的窮小子揣著僅餘的幾塊錢盤纏到了紐約,憑著運氣一夜成名,自此翻身。大衛信了,但是他的車不信。車在得州就拋錨了,大衛頭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修車上,但最終只抵達了66號高速公路的東岸終點聖莫尼卡。東海岸的海風吹涼了他的心,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2001年大衛18歲,血氣方剛,9·11之後兩個月,被責任感沖走的他選擇入伍,報效國家。他成為了海軍陸戰隊第二師第二營槍械連81排的一位普通戰俘,駐守在加利福尼亞州。“我愛海軍陸戰隊,它是我這輩子做過最驕傲的事情之一,駕駛和點燃高昂的槍械感覺也很棒。”這股對軍事對槍械的熱誠成為他自幼為數不多的高光時刻。
發表文章/道臣嵐
即使入伍的經歷,即使自身的個性,大衛對待那個世界的形式和許多人,甚至許多女演員都相同。面對這些旁人覺得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他卻曾經多次即使對現實生活、對名利的婉拒,差一點點就失之交臂。他經常和他們深入探討自然主義,問他們為什么要在這兒,為什么要做這件事,跟我有什么關係?
7歲那年,大衛·德賴弗的雙親再婚了,他跟著父親從加利福尼亞州的哈瓦那搬回了賓夕法尼亞州的米沙瓦卡。這是一處很傳統的英式小城,大衛家裡也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就連他這位出任助理辯護律師的父親也選擇與長老會的神父再續姻緣,可他他們並不討厭宗教信仰的束縛,甚至在這種的環境裡深感很多無法融入。他遠離生母,又不了和祖母處好關係,早早步入了父位缺失的狀態;無心課業,也就無法領到令父親滿意的戰績,這也引致後來他在家中話語權持續走高,甚至要支付在家的租金。
他曉得他們須要保有做為女演員的幽默感,和配角維持安全相距。“我的工作就像特工,活在社會公眾眼前又要過他們的私生活。當你發現他們成為眾人焦點的這時候,一切都顯得很艱困。”他堅信女演員的本職是隱藏在人群中觀察生活,“假如你來到一個臥室所有人都看著你,這可沒什么幫助”,並始終認為“與世界性的問題比起來,關於我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大衛和喬瑪麗對錶演的意志濃縮在AITAF的每一場演出中,持續迄今。他們向部隊數據傳輸當下社會的思索,也和女演員分享軍營獨有的人文。大衛沒能順利完成自己的軍官使命,他將此種為人民服務的意志注入表演,注入“服役”終身的事業裡。
與丈夫共建“軍中表演藝術”把舞臺搬入軍營
《婚姻故事》不僅讓他提名奧斯卡金像獎,征戰各大世界性的影片大獎,並且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華金·菲尼克斯的親口好評,也被弗蘭克·斯科塞斯誇作“這代人裡最傑出的女演員之一”。但那些名利從不是他主動追求的,他更希望他們活得像個隱形人,享受和丈夫在一同的紐約客時光,也漸漸意識到為人母的職責,開始學著調整他們的生活節奏,儘可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那位前空軍戰俘的概念裡,個體永遠是微不足道的,關鍵的是你為團隊、為族群、為世界帶來了什么。他永遠覺得他們做得還不夠好,也永遠在讓世界顯得更幸福許多,更寬容許多的馬路上。
很多人說散文能把內心深處的價值觀用更為雄偉威嚴的方式傳達給你,他就是以此種形式詮釋我寫的配角和臺詞。類似於德尼羅和帕西諾那些性格演員。——《婚姻故事》編劇諾亞·鮑姆沃爾夫岡
但是,逐漸下降的知名度和經典作品配角帶來的光環毀了他曾享受的匿名性,工作不再僅僅關於故事情節和配角,還有紅地毯和頒獎典禮。《星球大战》系列在他的履歷表上刻下了驚人的電影票房戰績,也使他徹底喪失了和現實生活的安全相距。
大衛·德賴弗榮登《好莱坞报道者》
他的臉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凱洛·倫充滿著對立和掙扎,通過他的演出就能看見配角經歷過的傷痛。——《星球大战》編劇瑪格麗特·甘迺迪
“對於沒有參過軍的人而言可能將很難理解,被知會無法參予軍事部署,對我而言是一種吞噬。”當同袍們在外保護祖國的這時候,他什么也做不了,併為此失望和愧疚了許多年。直至後來在同袍的開導之下,他才從此種愧疚中解脫出來。
影片《婚姻故事》片花
是演出再次挽救了那個格格不入的女人,他在這些和部隊沒有一點關係的劇作家、配角和經典作品中找出了一種與部隊經歷相關的共鳴。“只好我顯得不那么保守好鬥,開始能用詞彙表達體會,並且意識到詞彙是多么珍貴的工具。”
好在這一次他考進了。但是步入茱莉亞大學並沒有消除從軍營到社會的鴻溝,他依然有一段很長很複雜的心路歷程要走。當他在練習“給他們接生”之類的演出時,他的朋友們都在服役,此種落差常人難以想象。“我也不曉得怎樣大將部隊裡學到的科學知識或是思想層面的東西應用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我須要打零工,可沒有幾份工作跟打槍開火扯得上關係;思想層面呢,我掙扎於找尋象徵意義,在部隊裡每件事都有象徵意義,要么是遵從傳統,要么是有明晰的實用目地,比如說禁止抽菸是為的是防止曝露位置等等。”
參演安德魯·賈木許編劇的《帕特森》。
展望新的兩年,他說:“我希望他們能在2020年消亡,被人徹底遺忘,這種我就可以收到其它很尤其的工程項目。休假時我一般來說都儘可能維持低調,即使真的無法忍受自己對我的注意,我討厭隱姓埋名。”
可惜,大衛沒能實現報效國家的軍官夢想,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一年多之後,即使在一場山地車交通事故中摔壞了下顎,他被擔架抬出了軍營,自此告別軍隊生活。
離家出走獨闖荷里活,結果半路回來
希望2020年徹底消亡的心願,或難實現
“我想,假如締造出一個空間,融合這三個看似相同的社團,為現代人帶來一場休閒活動,該有多棒。基於自己的職業,去深入探討許多引人深思的話題,而並非強制觀眾們笑的小品。比如說故事情節裡這個‘被志願’參軍的少女;比如說設定裡這個提問關於盛行人文的問題就能獲得約會的該遊戲,結果卻是和一名未婚且正在哺乳期的拉拉隊副隊長結伴玩耍,那些都是懷著善意,同時又有一點小侮辱的戲。它們讓話劇呈現出的人物不再居高臨下,而是更為平易近人。”
在軍營,體悟女演員與戰俘的共通之處
也是在那個前夕,精確地說是在茱莉亞大學的第三年,他邂逅了未來的丈夫喬瑪麗·塔克。能肯定地說,那位老伯參予並幫助了大衛通向社會人的“馴養”過程。“她是一個很沉著的人,不能容許任何胡鬧。”喬瑪麗在大衛內心深處是一個學富五車的睿智男性,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芝加哥客。她天主教會他怎樣融入芝加哥的大都會生活,他則跟她分享滾石樂團有多酷。三位女演員融合了芝加哥客和軍官的特點,在2008年設立了一個慈善組織——“軍中表演藝術”ArtsintheArmedForces,縮寫AITAF。
AITAF最實驗性質的地方就在於,他們集結了一大群有天賦的戲劇女演員,用內容來政府軍他們,儘量減少製作效率,沒有佈景、不租服飾、不打燈光,舞臺可能將是百老匯的小劇場,也可能將是軍營裡的咖啡店,那兒只有兩排女演員朗誦對白,肢體演出,將所有焦點放到內容本身。“向大家展現,任何環境都能變為劇場,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和一大群完全陌生的人同在屋簷下,提醒我們自己的人性,提醒我們自我表達和肩上的來復槍擁有同等的價值。”
看話劇《报应者》的這時候我就在想,好傢伙,你做到了!那個小孩會成為明星!就像我是個獵頭經紀人一樣,我未曾對一個人的成功深感如此驚喜。——《弗朗西丝·哈》和《小妇人》編劇格里塔·葛韋格
同袍在服役,他卻在練習演出“接生”
《都市女孩》片花
文章標簽 都市女孩 星球大戰 帕特森 小婦人 弗朗西絲·哈 星球大戰9:天行者崛起 報應者 週六夜現場 婚姻故事 好萊塢報道者 酷刑報告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