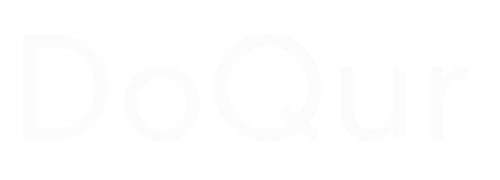編劇婁燁的經典作品裡,人物以遊走社會邊緣的姿態發生已成常規
成婚當日忽然跌倒的林慧已經使得“不可控的肢體”初現端倪;即便姜紫成歸來接她入院,三人在汽車後座聽著姜昕的《夜》,林慧看似放鬆地摟住了三個女人,在拿著攝影與汽車高速行駛的多重搖晃中仍變得恍惚易碎。宋佳出演的林慧在電影中顯示出一處峭壁的靜止質感,她的裸背是對男性皮膚的藉助也是對男性身分的感知,此種感知較為直白地對自我信念進行了保留。
連阿雲的失子、林慧的護女與小諾的“弒父”相對應,做為男性的她們都未曾因生育被編碼進家族鏈條,但三人的歇斯底里都應和著戴安娜·米利特所言,即“她們代表著被罷黜的母權制力量,雖然她們已淪為悍婦”。電影中的男性做為難以佔據、取用和分享空間的男性,無地可依,無處可去,常在混亂中面臨一種心靈與信念均被中斷的危險。這一中斷也許指向喪生,也許指向對自身的忘卻與背叛。
在婁燁的經典作品裡,人物以遊走社會邊緣的姿態發生已成常規,張家棟那個“以父之名”的警員配角是電影的堅硬切面。除他以外,其它人物都處在基於日常永不停歇的異化中,並最終與此共趨隕滅。市場經濟帶來的化學物質豐盈相連接著個人貧乏,孤獨感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家庭生活裡被放大。張家棟與父親,小諾與母親,小諾與祖母這三對親子關係都無對接與澄清。
婁燁像呈現出建築物空間通常展現出皮膚,做為一個對陰影情有獨鍾的編劇,他在此延續了光影之中陰影隨行的優雅。不厭其煩地用特寫攝影機呈現出由面容為載體的落淚、笑容及微不可見的疼痛。蠟燭、路燈、霓虹燈這種光度嚴重不足的光源藉由地板再照到人物臉上,使臉部關節的起伏成為人物內心深處情緒起伏的對照。在中近景攝影機中,緊張的肢體透出現代場所的瀰漫性恐懼。整部影片中的人物動作毫無舒展意味,肢體的緊張感貫穿全劇。
林慧對張家棟的愛護與小諾對張家棟的傾慕並無相同,這對母子對張家棟點到即止的藉助和難以遏制的憐惜,都指向她們對自身的這種尊重。那種與張家棟此類女人並肩而行的期盼,事實上是對另一個不再混亂的自我的期盼。在家庭空間中受到暴力行為威逼的林慧被妻子從臥室拖到廁所,再投進精神病院;難以維繫情慾關係的連阿雲被戀人驅逐出車,最終陳屍河邊灌木叢;小諾做為小小兒子,在看似光輝的衛星城空間裡輾轉玩耍,最終在高樓下砸毀祖母鋃鐺入獄。
從《危情少女》到《花》,婁燁熱衷於刻畫自毀信念極為強烈的男性,並使她們最終難以克服發生於自身的異化,與其同歸於盡。更重要的是,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裡,此種危險被處理成了毫無遮蓋且高歌猛進的質感。男性皮膚在整部電影中成為特殊空間,成為進行反抗的場所,但隨著男性皮膚的損壞、被佔據與最終殞滅,此種難能可貴的反抗性最終走向流失與滅亡。
從林慧、小諾到連阿雲,觀眾們難以完全尊重其中身陷癲狂又情愛勃發的女性配角,更難以不對姜紫成或唐奕傑這種的男性配角抱有鄙夷之感。年長警員張家棟做為歌劇上的技術性讓步,為觀眾們的尊重提供更多了支點,但與其說他是真實可感的人物,不如說他是電影向觀眾們拋出的橄欖枝。一個走上逃亡之路並揹負母親之謎的年長女人,因兼有歸降管理體制的身分而變得可疑——男權給出挑戰,對他回答,逼他投奔,又獲得他的歸降與臣服於。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