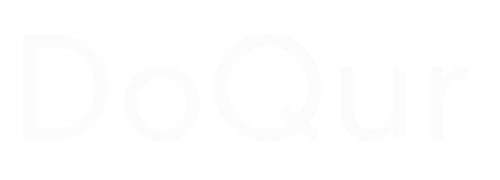拉胯!《哭悲》被封禁詞條,是誰為君主穿上的新衣?
結果,它拉胯了。
正如編劇賈宥廷所言,這影片就是為的是拍“凶殘”:
彼時許多新聞媒體拿《哭悲》和《釜山行》較為,送給它封了個什么“中文版仁川行”。
誠然,我曉得整部《哭悲》原本也沒打算面向全數觀眾們。
痛感也並沒有丟失,自己會感覺到累,感覺到痛,甚至還能在被病毒感染的情況下感受到一些皮膚部位的變化,進而享受魚水之歡。
甭管它是被推上來的,還是他們踏上來的,此種宣傳與實物的錯位,最終還是消費他們,噁心了別人。
當時覺得,影片製作教育經費不高,比不上拍一部非常緊張、很暴力行為凶殘的電影,來展現出人性中的哀傷悲哀 —— 只好就寫成了整部“禽流感、病原體、殭屍、人類文明失去人性與理智、恐怖、凶殘的電影劇本”。他說,“我想攝製一部影片,受到這種病原體感染,激發出人性最惡的另一面。
——全文完。
就連《南方车站的聚会》都有“雨傘穿胸而過,迸發出漫天血花”的絢爛場景,而做為一部舉起無底線的粉絲專供片,卻在本應簡單展現出鏡頭的故事情節遮遮掩掩。
它是一部廉價的獨立影片,是cult,是小眾,是挑觀眾們的。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不過,儘管劍走偏鋒,但好歹三部影片野心上佳,立意深遠,畢竟沒嚇到觀眾們,跟什么“恐怖電影二年”很多落差,但最起碼還稱不上爛。
為的是表現此種思緒,編劇還尤其設計了一段超現實的戲碼:
總之就是故事情節、恐怖、創意設計上,都沒什么可圈可點的地方,也但是一些外型尚可罷了。
可偏偏,這故事情節只是編劇釋放壓力的大背景板,故事情節一條路走到黑,就是兩對戀人在騷亂下的自救,
此種慣性主導了我們的思索,模糊不清了暴力行為與理性的界線,也在淡化道德感的力量,這只不過是一個較好的寓言處理,它表露了暴力行為只不過藏在每一正常人的皮囊之下。
警員拔槍亂射,播報員汙言穢語,小學生輪番欺凌,這些紅男綠女們,自然也步入了繁衍時節。
倘若導演從那個終點下筆,深入分析政治體制與個體的關係,那電影可深入探討的方向百花齊放,大有發展前景。
那么,一個完全沒有道德感的人類文明社會,會變為什么樣呢?
說白了,自己就是被剝奪道德感的“人”。
賈宥廷本名Rob Jabbaz,是一位加拿大人,本職工作是一位特技師、動畫師和獨立電影人。
”。
想洗澡就喝,想砍人就砍,沒有羞愧沒有疑慮。
。
“
這五部影片並非領到許多小大獎就是在電影節贏得前所未有迴響,現代人口口相傳,在自主安利下催生了一場恐怖電影的狂歡。
儘管沒看見實物,卻應和著造勢,鼓譟起一陣陣限制級熱潮。
看見這兒,編劇所表達的主題也就不言而喻了。
要說君主的新衣,《哭悲》必須是穿得最少的一個。
於是乎,現代人饞了,《哭悲》火了,都引頸盼望著這一份紅黃相間的限制級大禮包。
論奇絕,它遠不如偵探伯格,論恐怖,它遠不如大衛哈里森,論美學,它更是拿不出手。
我曾試想過,倘若《哭悲》沒有被新聞媒體穿上君主的新衣,在一些專項影展領到獎後,悄咪咪來到市場。
但,誰讓它踏上了舞臺中央呢?
我還曾幻想過,倘若有一大批自帶抗原的人,在維持理性的情形依然把他們偽裝成感染者,進而給他們一個實行暴力行為,滿足慾望的藉口,也未嘗並非一段更讓人揪心的故事情節。
到了整部《哭悲》,這“恐怖電影二年”的榮譽稱號,就成了貶義詞了。
砍砍砍,追追追,僅此而已。
在臺南縣公映時,它還曾曝出:觀影前夕有1/3的人因無法忍受而離場。
縱然有耳朵,縱然在現場,但現代人或許都是“失語的”。
首先而言,它肯定並非國際標準象徵意義的喪屍片。
隨著那些影片揭開神祕面紗,觀眾們爭相開始懷疑這口碑從何而來。
就當《哭悲》立刻掉出及格線的這時候,某瓣居然把它封禁,點進來的詞條已經變為“未知影片”。
隨著資源流入,《哭悲》立刻被放進展櫃哄搶。
此種程度還真稱不上更讓人“感受到恐懼”,更配不上它花團錦簇的名銜。
但是與鑼鼓喧天的造勢融為一體的是,《哭悲》在某豆打分開分也不過7分,僅僅三天時間後,更是光速滑落到6.1,依照態勢,整部影片最終平均分也不過是5分多點。
《南巫》、《灵媒》、《哭悲》和《咒》。
上了滑行道還束手束腳,當了X子還立什么牌樓?
爛中再爛。
《灵媒》號稱中泰三位大神合體,結果拍成電影“攝像師的自我學識”,主人公被咬成篩子仍舉起攝影機,以偽記錄片的模式向世人科教了攝像師的行為準則。
而這些幫忙造勢的“專業影評人”又事了拂衣去,再度策畫下一場狂歡了。
巴士上出現捅人該事件,從開始到爆發,圍觀廣大群眾居然除了尖叫聲以外,一句對白都沒有。
2021年,有人說是“亞洲地區恐怖電影二年”,理由是有五部分別由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中國臺灣的恐怖電影面世。
誠然,即使專業對版,《哭悲》的外型完成度極高,許多場面也可圈可點。
在媲美文藝片的長鏡頭下,盡情浪費著觀眾們好不容易簇生的腎上腺素。
可觀看完整部片後,我覺得首先要幫影片中的感染者下一個定義。
明明打著恐怖暴力行為的旗號,卻在許多場面使用迴避處理,猥瑣男愛上眼珠的打戲也就而已,連磨具和砍頭的鏡頭也略過,療養院的蜈蚣交歡只敢給局部,連個總體全景都沒有,實屬很多小家子氣。
緊接著,新聞媒體打出條幅:
正如巴士上的猥瑣男來說,他指出網絡時代下的道德感已經成為枷鎖,當下社會的現代人都習慣性戴上面具生活,把臉藏進智能手機中隔離真實世界,在不斷敷衍對方與打壓他們的匹敵間隙中苟活。
嗎有人病毒感染了?
由此可見,編劇是有野心的,至少看上去如此。
即使同樣有追車戲,再加上《釜山行》關注度未過。
正如片頭的病毒學家所言,感染者只是被打壓了邊緣系統,自己所有的動作都指向一個最終目地——滿足慾望。
比韓國更變態,比歐美更恐怖,口味之重更讓人側目,“恐懼”、“獵奇”、“陰影”等詞語一股腦灌輸,就差講出
論語言:
但是期盼越高,沮喪越大。
但是,做為早就看完十大X片,在各式各樣西式英式血液浸淫下成長的我,甚至是螢幕前的你們——
接著,這些粉絲們嗨了,自新聞媒體們瘋了。
很似乎,劇中的配角被病毒感染後依然有理性存有,能說話,能溝通交流,能理解,甚至能思索出登陸作戰計劃。
公映前,它說是被金馬拒收(只不過是沒過第二輪),公映後它說是被網飛拒收(只不過是品味與網絡平臺不符)。
更何況它還夾雜著那點思之更讓人發笑的私貨。
要問怎樣,所以並非即使它“名符其實的噁心”,而是在質量奇爛之餘,還夾帶著製作者臭味的私貨。
的評價。
不看《哭悲》枉為恐怖電影粉絲了
而此種慣性思緒牽引著觀眾們,當療養院出現暴亂,當女主沉湎於暴力行為時,我們也會訝異:
《南巫》更是披著恐怖電影的皮,實則是編劇對故鄉的託思懷想。
《哭悲》
現在,是這時候扒下這君主的新衣了。
而且我們看見,為的是反抗此種束縛,即使在病毒感染之後,那些帶著社會記號的配角們依然沒有忘掉他們的身分,反倒依照身分進行了專項報復——
拉胯,拉胯,拉胯。
“我發現了一個巨牛的片兒,居然華語能拍出此種!”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