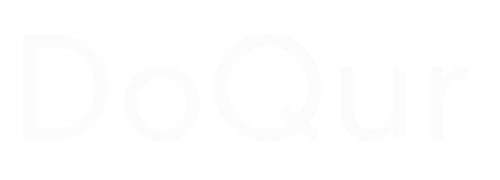一個幾乎被男性壟斷的行業,定價權開始向女性傾斜
《过春天》片花
她們從男性的身分出發,對現實生活的情況,有別樣的思考和很強的同理心。
曾贈在拍《明月的花园》
當年寫完電影劇本,王一淳醒來沒專業,沒大背景,沒知名度,沒人給她投錢,得靠家中支持。拍出來又沒錢做中後期,只得閒置在家中。
電視節目裡,她最終一路逆襲,從來不被看好到奪下了最低榮譽。
她藉著生日的由頭,寫了好⻓的告別辭,準備酒過三巡,告訴朋友們,她不幹了。“臨到關頭,我一看我們聊得挺高興。沒必要搞得這么感傷。後來想再堅持一下吧,我就賴著沒走。”
不止一個人有這種的困惑,在學院的北京電影學院裡,男女的比率是差不多的。為什么步入行業後,男性會一個又一個地消亡?
“我們這一代人,是看動漫和聽搖滾樂長大的,你說這種成長的男孩當媽後,怎么還會跟以往操勞、隱忍的父親一樣呢?”
麥麗絲,代表作品《悲情布鲁克》《天上草原》
曾贈說:“過去我拍戲是很凶的,非常強勢且不太好商議。在一個全數是男性值班人員的內部結構裡,我天然想去政府軍他們的女性身分,害怕受到批評。”
領到“本年度價值編劇”的是女編劇曾贈。
曾贈在拍《云水》
2015年,她38歲,一波三折地交出成名作《黑处有什么》,領到FIRST最佳男配角。姜文評價她一個字:壞。“獲得那個評價,我很自豪,打算好好幹上一場。”
《送我上青云》的編劇滕叢叢在其它新聞媒體的專訪中說,以前在劇組,有人問她抽不吸菸,喝不飲酒,唱不唱K,她都婉拒。對方的反應是:“你這種當不了編劇的。”她不信,她堅信一個好的故事情節,就可以關上這扇門。直至有一天,姚晨看見了她的電影劇本,決定做她的製片人和男主角,幫她找來傑出的聲音、剪接和攝影。
曾贈的運氣很不太好,每逢拍片,必下雪。首支《爱情》在荒漠裡拍,居然也下雪。片場沒有預案,去現場一看,景都成了泥。製作時間因而被大量壓縮,曾贈只能熬。
但是,當我們繼續探求,會發現,
我們經常提到“地板牆壁”。在職場中,一個透明的,似的不存有的,但實實在在負面影響男性的經濟發展的障礙。在影視製作行業,這被叫做賽璐珞牆壁,指男性數目的嚴重不足。一種被許多人普遍認可的,刺破賽璐珞牆壁的形式,就是“運用手提包的力量”,支持男性編劇的經典作品。
“有一回張大磊(《八月》編劇)跟我說,他要回內蒙古,去寫個電影劇本,順便帶小孩。我一聽就笑了。有小孩根本沒可能將的,整個假日毀於一旦,還想要搞表演藝術。”
中國電影史北美票房前100名,由男性獨立主演的,只有三部。除了《你好,李焕英》,還有排名第一53位的《后来的我们》。而賈玲和劉若英,都是從女演員轉型做的編劇,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女演員”身分的電勢。
在我們的專訪裡,創建公平和信任的工作關係,是較常被提到的詞語。
德格娜站上FIRST領獎臺時,剃著寸頭,肚子裡懷著老二。
兩條專訪了多名青年女導演,
除了一桌跨年飯,她們沒有組織過一場飯局用以搞關係。片場關係融洽,她們發言細聲細語,但沒有人會因而鄙視她們的意見。
邵藝輝《爱情神话》、申瑜《兔子暴力》,
才最終被看見?
那個選擇,意味著她無法進行高強度的工作。在之後的7年時間裡,她沒有任何一副部長片面世。直至她上了綜藝節目《导演请指教》,許多專業人才想起她的存有。
2021年的院線劇中,
她2016年就“出道”了, 當年“壞兔子影業”發佈了“新人編劇支持計劃”,有文牧野、路陽、荒漠、溫仕培,兩排男編劇裡,1987年生的曾贈是唯二的男生。
2022年公佈的賽璐珞牆壁調查報告(The Celluloid Ceiling Report) 顯示,2021年top250的影片的製作團隊中,94%沒有男性攝影師,73%沒有男性剪輯師,72%沒有男性導演。
也許曾贈的一句話,很適宜女導演們的心境:“當我曉得順利完成一件事情,要經歷困難和綿長的等待時,我會在心底一直反擊他們,對未來很喪,但很難被打倒。”
父親麥麗絲是青海製片廠的編劇。兒時,德格娜被放到奶奶家照料,父親在剪片子的中間回去看她一次,馬上再去劇組,這一去就是三四個月。
“我在缺少同情心的環境里長大。跟我父親抱怨過此種陪伴的缺失,也會覺得她經常不夠理解我……”
即使她們的冒頭,我們才有了這種的經典作品:關注家庭中父親的境況的《82年生的金智英》《暗处的母亲》《平行母亲》……關注性侵、墮胎問題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日本之耻》《前程似锦的女孩》《正发生》……
對女性而言,拼皮膚並非一件難的事。但片場一直以來的運作制度,多半由男性來制訂,遵從的多是男性的體能、習慣和社交形式。
均由女導演贏得。
即使在北京市區21點後無法攝製,自己沒有熬大夜,沒有趕工,每晚都是一大早動工,早上9點前準時收工。休息間歇,我們就到馬路上喝杯咖啡、吃碗小餃子。女演員們每晚像上下班一樣來拍片,收工就騎個車、散個步回來喝茶去了。
《我的姐姐》裡,雙親過世,要照料哥哥的妹妹
曾贈的影片《爱情》片花
王一淳接受“兩條”專訪
在國內,講兩性、母子之間複雜關係的《她房间里的云》《春潮》《柔情史》《兔子暴力》,少見又自如地展現出中女感情的《爱情神话》,講婚姻關係選擇的《金都》,講青春的危險、曖昧與懵懂的《过春天》,和講生育經濟政策下沉默的“妹妹們”的《我的姐姐》……均出自於男性編劇之手。
曾贈第二副部長片《云水》
遠遠比我們想像得少。
“有時候編劇也沒辦法掌控一部影片的宿命。影片工業是這種深不可測,我只是其中的一個⻮輪。 ”
她想揭開困局中的男性會經歷的痛,被無視,沒有被較好地對待。《我的姐姐》的封閉式結局引起爭論,批評妹妹還是要為哥哥犧牲。但這恰恰是男性製作者的珍貴之處,給男性以支持而並非支配。
“告訴男性必須怎么做,是不公正的,即使你沒有處於這個男性所處的位置上,沒有面對的她的這些對立和艱困。”
為的是獲得團隊的信任,男性編劇要適應這種的節拍,甚至做得很好。
男性從業者的數目和認知度,
“後來那張光碟成了我老婆爭吵最強有力的證據。無論即使什么爭吵,如果他一說,看!這就是我們家最貴的東⻄,兩張300萬的光碟!我馬上就沒話了。”
但等到王一淳交出第三副部長片《绑架毛乎乎》時,已過去7年。那些年,她仍然是家庭主婦,先花了一兩年寫新的故事情節,過程中想去家政公司體驗生活,但苦於沒人給她帶娃。
收到《导演请指教》邀請的這時候,曾贈、王一淳、德格娜都沒有遲疑。這是她們等了平均值8年的,被看見的機會。
依照《导演请指教》的賽制,短短几天內就要順利完成一個影片。
那是2015年,她31歲,憑藉著《告别》領到FIRST最佳故事情節長片獎。許多人以為這是她事業的終點,但她已經默默地決定,把精力放回家庭,多陪伴三個小孩。
很多編劇把30歲視作拍出首部經典作品的時間,而30歲左右的男性,許多正面臨著生育、家庭的重擔。在帶娃和家務間歇裡,擠出創作的時間。
戛納、維也納、那不勒斯影展的最高獎
都掏出了兼有男性意識和電影票房整體實力的口碑之作。
後頭一兩年,她一直在和勞方打交道,轉了一大圈,還是他們掏了錢拍。“挺曲折的,總有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一不小心耗了這么十多年。”
《爱情神话》片花
一組對比數字是,僅有4%的影片,團隊裡只有0-4位男性值班人員;但只有0-4個女性的團隊,那個數字是驚人的61%。
曾贈總是這種介紹他們:曾贈,編劇,女。
“那時候我整天就想去外邊遊蕩,過了許多年在育兒社會公眾號上看見,才意識到,哦,原來我當年是抑鬱症了。” 她體驗過那種被雞毛蒜皮壓到恐懼的狀態。只好她顛覆刻板第一印象裡的父親形像,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個生下小孩後投奔的男性配角,神祕、優雅又脆弱。
2021年末,她感覺他們生活在非常大的挫敗感之中。“來上海十多年,一事無成,那比不上搬到湖北算了。”
愈來愈多地發生男性的名字。
照料三個小孩,大的這個剛上中學,德格娜基本沒有懶覺能睡,家中根本不了安心工作。有時回家去亮點書,是她少有的屬於自己的時間。她會騎兩輛電動滑板車,夏天的這時候裹得只露出一雙眼,來去自由。
《兔子暴力》片花
德格娜的選擇和她的父親相關。
同樣在《导演请指教》上嶄露頭角的王一淳,1977年生,自稱為“大齡未婚女導演”。日常的生活就是接送小孩,照料真菌,在洗衣機上貼家務事的字條。
有人說,女導演的時代到來了。
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她成婚生子,操持家務。即使不願意把步伐停下來,她掏出破釜沉舟的決心,去廣州口岸做田野,沒人投錢也要拍。
《导演请指教》綜藝節目裡,
初出茅廬的殷若昕《我的姐姐》、
冠軍賽男女比例是驚人的1:4,
在電視節目中,曾贈第二次上場,被稱作“新人編劇”。只不過她做編劇有7、8個年頭了。但一開始,沒有女演員願意選她的組,即使沒有看完她的經典作品,她是陌生的,不知能耐的。
攝製碰到特殊情形,她說的最少的是“還好我們能陪我苦熬”。拍戲最自豪的時刻是“跟我一同工作,我們能感受到高興和公平。”
大多數這時候,德格娜就是在柴米油鹽裡“打生活的仗”。
長大了,德格娜他們當編劇才意識到,“事業有成的女編劇”和“經常陪伴小孩的父親”,二者不容兼得。而她選擇前者。
男性編劇的視角,即使稀缺,變得彌足珍貴。
王一淳碰到最大的難題就是皮膚。“再讓我拍一回,我肯定撐不住了。啊咬牙撐過來的,心底老惦記事,幾乎難以睡覺,靠吃藥就可以躺一會兒。”
《我的姐姐》收穫8.6億電影票房,編劇殷若昕決定拍整部片,是因為接觸過計生經濟政策下的“妹妹”。
《我的姐姐》的導演殷若昕、編劇遊曉穎、製片人尹露、執導張子楓都是男性。她們在一同工作,來源於對男性宿命的共鳴。張子楓為的是配角剪掉了短髮,殷若昕也把指甲剪短了,“和她一同同呼吸共宿命。 ”她會在閉路電視前流淚,拍哀傷的戲時告訴張子楓,“今天那場戲,可能會很傷痛。”
想看一看,她們都走過什么樣的公路,
夏天的早上,德格娜騎滑板車出行
在奧斯卡金像獎,被女性佔有的最佳編劇和喜劇片,
《我的姐姐》片花
這是史無前例的,全新的,屬於男性的時刻。
曾贈在《导演请指教》拍完4支影片後,每一次都會手寫所有值班人員的名字,“我記不住所有人的名字,但想向自己揮手致意。”
《黑处有什么》片花
除此之外,還有古老的規矩橫在路中間。曾有一名年長的女導演,在殺青典禮上特意正式宣佈,在她的組裡,所有男性都能坐蘋果公司箱(化解女演員或粒子高度問題的墊腳箱子)。男人坐蘋果公司箱,被指出會帶來晦氣,迄今仍有許多男性從業者即使趴在一個箱子上遭到責罵。
發表文章 | 洪冰蟾 責編 | 倪楚嬌
《爱情神话》裡中女們反客為主。現實生活裡,編劇邵藝輝和製片人葉婷,這三個新生代的男性,也“反客為主”地率領著一大群“老炮兒”。
德格娜去教區拍《巴德玛》
真人秀中呈現出的超高壓工作,是編劇的日常。編劇的工作時間,常常比996更漫長。依照“畫外”2020年的調查,“近七成編劇的日均工作時長都在8-12半小時之間,甚至有21%平均值每晚工作少於12半小時。”
《兔子暴力》的編劇申瑜是一名父親。她做完月子後得了產後憂鬱症,買了兩輛三輪車,夏天還在山腳下軋馬路,直至後來出了小車禍,才把車賣了。
德格娜有一次遇到曾贈,三個人都灰頭土臉的。“哪裡顧得上眼妝精巧,都沒時間睡覺了。”
憑藉著《过春天》,領到2018年平遙影展最高獎的編劇白雪,和德格娜同歲。
德格娜苦笑,跟曾贈說:“我今天中午去洗了澡。”曾贈回道:“我也刷了個牙。”
在其它新聞媒體專訪中,她說他們是“一個寫不出電影劇本的待業主婦”。“我為我小孩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但是你內心深處是很傷痛的。你會很想拍。”拍完後,她的感覺是“長出一口氣,感覺迎來了人生最好的這時候。”
“似的重男輕女那個東西,一直是隱隱地流淌在我們骨血裡的。4年前,我經歷了懷孕生產。有一次我在排隊等候產檢,聽見後面有一個已經剖腹產四次的男性,為的是生女兒,她現在又懷孕了,醫師就說我不可能將再給你剖腹產了,太危險。但那個男性一定要生,求著醫師建檔。 ”殷若昕說。
沒知名度、沒投資、沒聲量,還陷在生活的瑣碎裡,是許多青年女導演的共同困局。
我們也能看見男性之間的守望相助。
“曾贈是我他們,編劇是我的職業,男性是我的性別。我希望我們公平地看待編劇那個職業,我也十分高興他們是一個男性。”
李玉在青蔥計劃做導師,認領了三個女權主義的電影劇本,其中一個就是《兔子暴力》。她欣賞申瑜的天賦,幫申瑜做編劇,引導她即使不完美也沒關係,但是“要生猛”,“任性一把”,“順利完成他們想要的”。
女導演的存有,不但提供更多了關鍵的、常常被忽視的聲音,更有利於從業者的性別均衡。科學研究顯示,女導演的團隊中,男性成員常常比率更高。
文章標簽 兔子暴力 前程似錦的女孩 她房間裡的雲 後來的我們 柔情史 正發生 黑處有什麼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 金都 導演請指教 春潮 過春天 雲水 我的姐姐 平行母親 八月 暗處的母親 82年生的金智英 悲情布魯克 天上草原 綁架毛乎乎 巴德瑪 你好,李煥英 日本之恥 愛情 明月的花園 告別 送我上青雲 愛情神話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