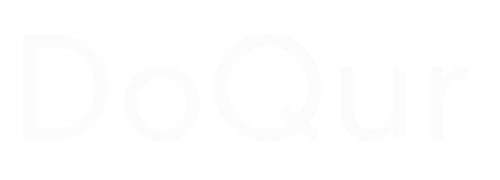賞析林超賢的經典作品藝術風格及主題,探尋澳門動作片背後特別強調的現實性
為的是化解生存困局只能與黑幫同流合汙,導致身分的邊緣化。同一個時期的香港電影中不乏發生香港迴歸前後混亂的社會心理使得警員隊伍人心動搖的情形,其主要即使個人屬性與社會屬性受到社會失序的衝擊,導致警員隊伍中很多人陷於身分困局和思想困局。
吳宇森的暴力行為美學著重唯美化和以降格攝影機的表現手法表現暴力行為和恐怖。同時期歐美驚悚片的暴力行為攝影機則變得遲鈍笨拙,而當時中國內地動作影片中的搏鬥場面又經常為中國武術動作的質感所負面影響,著重武打動作的設計而忽視了人物內心深處感情。
影片中人物的思想困局主要彰顯在心理障礙與倫理傾向上,這類具備心理障礙的警員形像之所以在澳門影片中大量發生,是因為經過澳門迴歸之後一兩年的平穩過渡,群眾從迴歸末期混亂的心態中趨於穩定,轉而將關注的重點由原來對身分歸屬轉向這些曾經被澳門經濟繁榮所掩飾的社會問題與群眾的心理問題。
當警員李滄東在面對喪失情人的悲憤下,最後閃現出了一絲人性的光輝,在揹負侵吞公務成本的信用風險代價下仍選擇將好處費付給線人。
做為香港電影中最為成熟的商業電影類別之一,警匪動作電影一般來說都涵蓋邏輯細緻的敘事內部結構和驚險驚悚的劇情,而此類影片更吸引人的地方是通過爆炸、打鬥等暴力行為場面呈現出的聽覺張力和它帶來的心理快感。
原先堅守著善良和使命的四個警員為警務處忠誠曾效力,由於警務處對其缺少職責和關愛,昔日誠摯為民的五人最終走向了對立面,由警變為匪。
在林超賢晚期眾多澳門警匪影片中,他對澳門警員形像的刻畫更加立體化,不再像以往一樣以細長、單調的公義形像示人,而是將警員刻畫成在他們內心深處潛藏著人性複雜交織且倫理困局的一類人。
由於黑幫性質組織的流行,社會治安讓現代人引發恐慌,時刻威脅著市民的生活與生命安全,現代人的價值觀念因而遭到衝擊和模糊不清,個體在社會公義與善惡情理之間徘徊不前。與此同時,澳門社會秩序的混亂引致部份警員的身分的社會屬性遭到威脅。
暴力行為常被看做是對別人導致危害的行為,而整部電影表達的是自我施虐與被虐,王偉業因難以接受他母親的死而性情大變,又因誤救了殺人犯韓江,人性感情糾葛與身分尊重雙雙被“心魔”所困。
從林超賢晚期攝製的香港電影經典作品中能發現,他熱衷於攝製警匪題材的動作類別電影。當電影類別被歸於警匪片或驚悚片,影片中就註定充斥著暴力行為武裝衝突,犯罪行為、打鬥、殺戮和槍戰等暴力行為元素。
在身分困局之下彰顯出身分的邊緣化,在思想困局之下則彰顯出價值觀念的邊緣化。
縱觀林超賢編劇攝製的澳門動作警匪電影,影片攝影機表現得無一不是展示出緊張刺激的槍戰打鬥場面,電影中充斥著爆炸、砍殺、追逐、搏鬥、廝殺等暴力行為元素。
影片《线人》結尾處線人細鬼和同伴以及歹徒等人在廢棄課室進行三組生死搏鬥,一邊是線人和同伴與歹徒之間用刀和木棍相互砍殺,在堆積成山的課桌椅中追捕,另一邊是警員與歹徒爭吵在地以拳暴擊並抓摳對方喉嚨。
通過心存做為的警員幫助淪為打劫者的舊日同事這一人物關係的設置,不但讓警員這一身分屬性顯得模糊不清,也是當時一種在當時社會環境混亂的社會秩序下對社會公正的批評和嘲諷。
影片的動作場面旨在突出暴力行為的慘烈與殘暴,散發出一種紀實化意味的恐怖感。
在這三場槍戰中,人物就像是處在鳥類階段和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之下,因接近於日常搏鬥中你死我活的常態,有種令人窒息的肅殺之氣,殘忍的動作場面將暴力行為與感情巧妙結合,以很強的真實感而給人很強的聽覺震撼和切膚之痛的體會。
他跟幫派稱兄道弟,幫警員擺平自己解決不了的幫派糾葛。正如影片中爛鬼東上司張警官的對白所言:
林超賢的澳門動作片通過反映人物邊緣化困局的敘事主題,引出警與匪之間矛盾的身分態度和生存困局而導致的暴力行為武裝衝突,通過營造沉鬱寫實的圖像空間,修復澳門當時生活的現實生活外貌,設計寫實性槍戰動作彰顯暴力行為紀實,使其電影呈現出具備現實生活主義藝術風格的暴力行為美學。
以下那些影片中的人物形像均彰顯了人性“善”與“惡”、情理與法理之間的思想困局。
“黑與白之間有一個棕色地帶,其實有的人佔地面積大些,有的人佔地面積小些”。
通過警員李滄東與“線人”廢噏、細鬼的感情倫理變化,反映了在社會中人的眾多氣憤和人性黑暗面;影片《魔警》通過暴力行為美學展現出了人性中關於神性與魔王的辯證關係。
線人最終被歹徒一刀刀砍在他頭上而慘死,鏡頭慘不忍睹,進一步演繹了暴力行為。
在警匪影片《重装警察》中四個警界菁英在倫理和法律條文的邊緣掙扎,在警與匪的配角間來回轉換。
林超賢編劇的動作動作片在經由《线人》、《证人》、《逆战》等影片漸漸形成了有林超賢個人民族特色的“暴力行為美學”。
他的影片在槍戰、打鬥等暴力行為表現上更貼近實戰化,人物的近身搏擊主要按照現實生活中存有的邏輯,武打動作無浪漫化的象徵表現手法烘托暴力行為的殘暴,使得其動作場景並有別於以往澳門警匪影片所熱衷於的唯美意境、拖泥帶水的套路與必殺技。
在現實生活社會語境下,林超賢編劇從真實出現的新聞報道該事件進行取材,以當時轟動整個澳門的“徐步高槍擊案”為大背景,翻拍創作出動作影片《魔警》。
比如晚期創作的電影《野兽刑警》最後一場兩人對戲份中,爛鬼東與圖釘華在街巷追逐惡鬥,被逼至絕境後在求生欲下本能運用周圍缺口的刀和樓房中的各式各樣生活物件做為槍械進行胡亂地搏鬥,在拳拳到肉和木棍砍殺的暴力行為攝影機下將影片推至最高潮。
在林超賢主演的晚期澳門動作片中,深入發掘了警員與歹徒在人性“善”與“惡”、“情”與“理”之間搖擺不定的思想困局。
1998 年林超賢編劇攝製的《野兽刑警》構築了兩條警與匪之間的棕色地帶,講訴了警與匪黑白相間的故事情節。其主角“古惑仔警員”爛鬼東遊走在黑白兩道的邊緣。
這則真實刑事案件出現的大背景是在 2001年至 2006 年前夕,警員徐步高因罹患分裂型人格障礙,在澳門所犯了幾起殺警刑事案件和一宗殺人案並導致四人喪生,因而被冠上“魔警”之稱。林超賢便以徐步高的人物性格為原型,在電影中塑造出一個內心深處有著魔障和思想問題的魔警王偉業。
賞析林超賢的經典作品藝術風格及主題,探尋澳門動作片背後特別強調的現實性。
在港英掌權至澳門迴歸末期,澳門混亂的社會治安給黑幫性質組織提供更多了不利的生存環境。
那些暴力行為元素也是十九世紀八八十年代中國香港影片興盛時期暴力行為美學中所共計的標誌性記號。在影片商業價值與表演藝術追求的兩翼下,林超賢編劇對動作動作片的把握能說是由外及內的。
比如在電影《线人》表達的核心是希望和恐懼交織的人性困局,影片中情報部門科的高級督察以汙點線人和人性的自私來經濟發展線人和蒐集情報部門,當警署李滄東看著他們的線人相繼被砍殺,他意識到警員與線人在表面儘管只是買賣,實際卻是以人性做交易。
在澳門警匪動作影片中,提到暴力行為就必然提及吳宇森的“暴力行為美學”。
但是林超賢編劇的警匪影片經濟發展則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暴力行為紀實”特點。
縱觀林超賢的澳門警匪電影,能發現影片的暴力行為藝術風格受到了澳門編劇林嶺東的暴力行為美學負面影響,其澳門警匪動作電影中常以爆炸場面和打鬥、砍殺、搏鬥等實戰動作場面帶來視聽上的暴力行為美學。
其經典作品機殼主要是通過暴力行為美學中激烈刺激的動作場面,以喪生、犯罪行為、打鬥砍殺等暴力行為場景來反映當時澳門黑幫的現實生活環境,和人文管理制度衝擊下所帶來的社會混亂與黑暗。而經典作品文件系統則圍繞人物的生存狀態、價值觀念取向、人物宿命展開敘事。
在林超賢編劇二十多年的影片攝製職業生涯裡,動作片創作的敘事主題幾乎是與澳門迴歸後的社會進程密切聯繫在一同,影片反映了澳門人在社會動盪不安革新中所發生的生存困局,涵蓋身分困局和思想困局。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