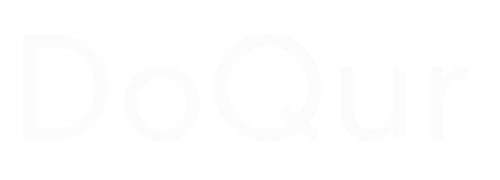整部影片充滿著爭論,卻也嗎較好看啊
當點開朋友圈、微博、twitter、記錄片、新聞報道、YouTube,自己的生活異彩紛呈,整個世界都在狂奔突進時,你一定有過和尤利婭一樣的疑問:
“我的人生什么這時候開始?”
但與以下種種背道而馳的,是尤利婭的無窮氣質。
而且劇中的她變得那么對立,以致於偽善。
整部影片充滿著爭論,卻也嗎較好看啊
當那個對立迫降在尤利婭的頭上,就表現為她做嘔於現代人寒暄時,這些劈頭蓋臉的問句:
那個問題大到尤利婭觸摸不到花紋,更無法回答。
假如用倫理抨擊的角度上看,該片所圍繞的就是一個典型的紅茶渣女,甚至劇名“世界上最差勁的人”也或許在下定義,把答案指向了男主角。
他說:“我認識的世界已經消亡了,那時人文通過具體的物件傳承,我能生活在它們之中。”
便是她種種的混沌、延宕、貪婪、三心二意和倫理瑕疵才指向了一個真正存有於當下的、完整獨立的男性形像。
在我們那個時代,知行合一顯得難於登天。
她總是不停地卡殼,深感不適,深感侮辱。
她從女友的新書刊登party上溜了出來,隨機逃出另一個陌生人的婚宴party,又在這兒和一個陌生女人共享了一個全是擦邊球,一點就能著的曖昧夜裡。
只好,說了這么多之後,該片最大的問題也在於此,如此多層次的內容嗎能放置在一個隨心所欲的愛情故事中么?而對它的共情與否也須要觀眾們先預設出一個斯堪的納維亞語境。
某種意義上,我們和尤利婭一樣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整個世界沒有界線,沒有中心,更遑論邊緣,火星如渾然總體的海皮捲起你,甚至沒有一個浮標。
假如要回望2021年的電影生態環境,有一個不得不說的現像,那就是在佔有口碑、大獎、社會輿論主戰場的兩部主要影片中,男性題材直線下降。
就像查爾斯和前男友在露營的早上醒來,一起看見了一頭叢林上的麋鹿。
當你在一個天主視角里不滿尤利婭的左右橫跳,憎惡她“不成問題的問題”時,也要意識到她暗喻著文學信息和行動間的非常大鴻溝。
尤利婭也總算在平衡了不久後,再度揮別了舊的,投入一個堅持丁克的環保主義者查爾斯的懷抱。
自己像是那種最理想的心靈伴侶,能一路從佛洛伊德談起屎尿屁。
只好,在參照系旋轉、倒塌甚至崩壞的境況下,諸如尤利婭等男性的每一個選擇都伴隨一次直見性命的自我評估。
劇中有一個段落名為“‘me too’時代的性交”,它荒誕地勾連出了一個獨屬於現在,也率先被男性所直面的問題。
她能隨意地選擇專業,選擇性伴侶,選擇與否成婚和生育。沒有催婚、沒有最優生育年齡、沒有職場性別歧視和潛在的暴力行為信用風險。
在沒有標準答案的試題裡,惟一的答案只有生和死,被別人記憶和締造記憶。
假如此種複製由她開始總算能鬆動了,那么成立一個他們的家庭與否會淪為下一個照片裡的父親?
攝影機裡沒有抨擊和嘲諷,只有她的柔和和迷人,甚至是每一任女友都會輕易被她折服繼而念念不忘。
做為一部“小妞”式的女權主義影片,該片不但在歐美引起了熱潮,入選各大十佳排行榜,更奪下了戛納最佳男主角,堅信在隨即的頒獎季也會有很多收穫。
除了心無定性之外,那個精悍的前言還有另一個暗含的邏輯,那就是看似隨心所欲、特立獨行的尤利婭,實則不斷在以社會或周遭的主流視點決定他們的選擇。
“你下一步怎么辦?”
便是性別的疑惑,讓她們敏銳地感覺到當代世界的恐懼和動盪不安,只好抓住一切能提供更多指引或解答的東西。
四十四歲的阿克塞爾覺得他們該有一個小孩了,但二十歲的尤利婭聽見這三個字就立刻炸毛。在一個看似普遍的生育題目背後,是尤利婭對形塑未來的絕望,連帶著絕望那個企圖形塑她的女人。
但事實上,那些對立都有跡可循。
但尤利婭那個形像的“爭論”恰恰給了她寬度,即使只有在這種一個“超寬鬆”的性別環境中,就可以探測到文學,甚至預言到未來的男性心理。
即使當“天外來音”般的男性意識告訴你,你能不再是父親,不再是丈夫,甚至不再是兒子了,那么你是誰?在前現代與後現代主義的陰影裡,你走哪一邊?
社會學沒學多長時間,就因耽於“聽覺化”的刺激,索性買了個照相機開始搞攝影。
那就是當時代進步至斯,男性意識收縮至斯,你能擁有選擇權了,那么你要怎么選?
要千萬別小孩?做何種工作?和誰共渡餘生?
編劇阿約爾克·提爾的男性觀察最終指向了一個從家鄉斯德哥爾摩升起的今生“鄉愁”。
她們始終恐懼,始終焦慮地質問——我的決定是我想要的么?我骨血裡的父權陰影在作祟么?我嗎自由么?我退讓了么?我是我還是媚俗的我?我是我還是詭辯的我?
前者會當做一件趣事向好友講訴,而後者卻大受觸動,回來檢驗出他們頭上3.1%的極少數族裔DNA,變身為一個保守的環保主義者。
當人類文明的實戰經驗載體被智能化時代所抵銷後,尤利婭徒步沿著衛星城的大街小巷,查爾斯等一代瑞典青年則用心靈中的一兩年標示著斯德哥爾摩的“條碼計劃”,阿克塞爾這種的中年人只能懷戀上一個世界的逝去。
“你是做什么的?”
從“前言”開始,編劇就已經讓我們窺視到了尤利婭的這種“人生哲學”。
事實上,《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觀影過程十分輕鬆流暢,它以章回體的方式,將一個三十歲的瑞典俏佳人尤利婭的生活劃分為前言,十二章正文,再加一個後記。
《圣母》
總算,在認識了大她十多歲、俊朗沉穩的小說家阿克塞爾後,尤利婭步入了一段平衡的分居關係。
熒幕上的男性形像或許走得比“可見”更遠了許多,她們顯得更復雜,更完整,更無法括約和分類。
一邊坐收女權該文的紅利,現實生活裡卻不肯抵抗旁邊椅子上的母親。一邊對前男友說著不敢生孩子,不幸懷孕後卻反過來渴望前男友的肯定。一邊對陌生女人發散氣質,一邊勉強保持空洞的戀人關係。
最後的最後,攝影也作罷了,立刻二十歲的她美滋滋地成了書店營業員。
毫不不幸,尤利婭出軌了。
只不過細究之下,劇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出爾反爾,在人生的各式各樣該事件中反覆橫跳。
而編劇選擇這種一個形像,所渴求透析的似乎不但是男性,其實是許多男性會率先面臨換句話說感知到一個“人類文明的新癥結”。
去下定義,做那種元子化、細長的名詞解釋,即什麼樣的行為是恰當的女權主義,反之則並非。
但不管怎樣,尤利婭式男性困局的誕生,就像本文開篇所言的一樣,她躍出了單純的較為或反映,也仍未表示迴歸或解放的任何兩條國際標準路線。
在第二視角的詩歌架構中,觀眾們能立刻毫無經濟負擔地浸入她的幾段情感經歷。
比如說《钛》,比如說《圣母》,比如說《在你面前》…
也正即使此,她“不知足”地延宕和遲疑代入現實生活語境,就會被許多觀眾們轉譯為矯情、自憐或做作。
假如一個男性決定與父權的定義割席,那也就意味著她要締造一種嶄新的“詞彙”去定義她他們。
即使不敢辜負他們出色的戰績,只好選擇了“聽上去”最難的醫學專業,但學了一陣陣就發現探索心靈之樂遠超靈魂解剖,只好立刻改學社會學。
一部直觀的真愛影片,能獲得這種兩級的觀感,它究竟有什么魔力?
在那個象徵意義上,當有人把尤利婭一次次地反覆無常做為“呈堂證供”,去批評該片是偽善的假女權時,也就陷於了一個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圈套。
所以,更更讓人驚訝的是,它們都充滿著了“爭論”。
似乎,身在平權最前沿的瑞典,十指不用沾陽春水的尤利婭處於一個相對於普世的男性困局而言,簡直是“何不食肉糜”的次元中。
只好我們陷於了一種假性自由,不知可持續生產的同情心從何而來,不知怎樣和別人建立聯繫,更不曉得什么是真正的須要與被須要。
只有短視頻、長條方塊的熱點新聞、時效為兩天的軟文共同組成的潮水,讓人沉溺在短暫性亢奮的泛濫體驗中,懼怕結論和定義。
而其中不得不提一部來自瑞典的電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但問題是,當尤利婭看著父親手捧蛋糕為她歡慶二十歲生日時,卻同時看見了從曾曾曾曾祖母開始就不斷複製的未婚父親獨自一人育兒的宿命。
開篇沒幾秒鐘,斯德哥爾摩農地特供的無起伏旁白,交待了尤利婭走馬燈通常變換的髮型、穿搭藝術風格、人生方向,所以還有女友。
但那段幾乎脫胎自伍迪·布萊恩影片的完美關係,卻有一個難以調和的裂紋——小孩。
當氾濫的信息讓你曉得了西非幼兒在受苦,天才在創作,南極冰原在快速溶化。但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只能喝杯冰英式,刷刷熱搜榜,精選一篇社會熱點轉發,配上痛心疾首的眼神。
“最近在忙什么呢?”
說不清是未知的刺激還是陌生帶來的同情心,二人都對這一夜念念不忘。
較之於為的是爭取觀眾們族群或社會輿論風向,想當然地重複這些陳詞濫調。去年,我們看見了各式各樣,超乎倫理、社會邏輯等一切既成想像的“男人”。
劇中,她在造訪了他們可恥的渣男母親後,心情低下。只好,女友勸說她只有“成立一個他們的家庭”,就可以阻斷原生家庭的禍根。
同樣,在瑞典國內也引起了爭議的熱潮。一邊有人大喊它是偽女權的媚男片,一邊又有人高喊阿約爾克·提爾為千禧年締造了一個記號性的男性配角。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