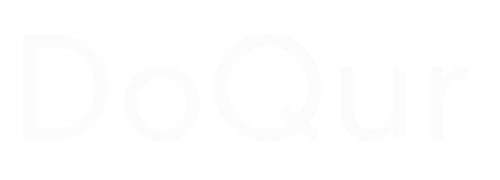訪談|《爱情神话》老烏飾演者周野芒:我想給你講個故事情節
《爱情神话》展現出的是成熟男女間的真愛,風趣也十分高級。但越去細品,越會發現劇中的老烏,做為站在老白身旁的這個“男人”,二人間的友誼同樣令人為之動容,更讓人不由得感嘆:女人永遠難以捉摸,男人至死都是孩子。
《爱情神话》此次找女演員,先決條件是會講北京話的北京女演員,以男性居多。女一號老白身旁的左鄰右舍須要有人來幫襯一下(笑)。
比如說我幫老白策展,一次沒用,兩次沒用,四次他還反感意,到了第4次操持又被他婉拒了,那老烏肯定就窩火嘞,搞什么搞你?廣州話是,“你怎么那么難伺候?”上海話呢,叫“迦門/茄門相”。老烏、老白間的此種互生反感,詞彙上要兩層兩層推上去,最後才會有這場“拗斷”的爭吵。
而上海話常常同一個意思有許多的表達,哪個是最準的,哪個是影片裡那個人物要說出來的,比如說都是講喝茶,“吃中飯、吃小食、吃夜宵、吃老酒”都不一樣。我們在做案頭的這時候,就拼命地去琢磨必須怎么去說。
雖然李志輿同學沒有教過我,但我在上戲的這時候看完他在《雷雨》裡演的周萍。他一上臺,你就能感覺到他的光彩。李同學演的周萍,必須是我看完這么多版本的《雷雨》裡,演得最好的。要說周萍那個人物是不討觀眾們討厭的,也很難在這齣戲裡給觀眾們留下尤其的第一印象。那個配角外在和內裡都是憂傷的,雙眼裡沒有光彩,但是是個滿嘴謊話的人,是一個非常窮困潦倒負面的形像。但李同學把那個人物的思索過程展現出來了,他演得讓人會去疼惜那個配角。讓觀眾們會覺得,哦,怪不得瀿漪、四鳳都會愛上他!他頭上儘管有病態的另一面,也有他們的氣質。那個氣質是誰的?李同學的。
我跟徐崢的關係尤其久遠。她家原來也是在安福路附近,我的單位(北京戲劇藝術中心)也在那裡,後來又是徒弟,又是同事,又是街坊。心理上尤其熟識,他挺討厭我,我也很欣賞他,除此之外我們在個性上也有共同之處,彼此間都希望能有一次戰略合作的機緣。此次,他就把我推薦給了編劇。
那齣戲叫《明日要出山》(1989年),是一個環境話劇,沉浸式的。當時他就趴在第一排,我曉得他那個這時候是很想考話劇學院的。我曉得他,但還沒有打過招呼。我就直接用雙眼找他用對白跟他溝通交流,那個這時候女演員的對白是要跟觀眾們說話的。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尤其深刻,四隻圓圓的大雙眼(笑)。他後來也時常提及這一段,四隻雙眼直勾勾地看著我。這個戲(表演環境)是很開放的,從街上演到我們大院裡的空地上,再演到小劇場裡頭,小劇場裡是把觀眾們席位置全數拆毀了,把舞臺放到中間,觀眾們還能上臺就坐。編劇是英國的一名環境話劇的大師。
片頭這場皆大歡喜的家庭聚會上,老烏總算向眾人道出了埋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真愛希臘神話”——一段他同西班牙國寶級男演員間莫須有的“拜占庭假期”。翌日一大早,眾人醒過來後發現老烏已經含笑九泉。他們一邊懷念老烏,一邊集體觀看了費里尼編劇的《爱情神话》(1969年)……
【下列是周野芒口述】
完全用官話來唱歌,對我而言也是第二次,更何況是用北京話來演。對於我而言有一個很好的便捷,無論怎么說,我是在那個環境中長大的,這數十年的生活,我頭上這兒的生活氣息是甩不掉的,總會流露出來。但是真正的地道的北京人,我接觸也挺多的。
《爱情神话》片花
比如說“賺錢”,以前叫作“賺外快”,過了一兩年又叫“搖張”,後來又變為“拉分”,那些變化都尤其的形像。市場經濟下,我們都是發工資,後來開放搞活了,很多人有了“外快”。“搖張”就是數紙幣,這就表明現代人開始富足了,手頭有閒錢了。再後來“拉分”,“拉”和“搖”的動作就不一樣。哎,要費些勁了。
所謂北京的老克勒,“克勒”是英語詞“colour”。形容這個人頭上、經歷色彩斑斕,加個“老”字,形容他到了極致,沒人少於自己那么講究。北京人之後的確有一部分人,說半吊子的洋文,叫“洋涇浜”,在公共租界英商裡做事情。聽自己發言也有趣,比如說“水泥地”,自己叫“水門汀”,是“cement”的譯音。再比如說,那些人回家討厭帶手杖——老烏就沒有拿手杖,管手杖叫“司的克”,一聽就是英語“stick”嘛。那個這時候還沒有電吉他,自己只會玩大提琴,大提琴不難學的,而且形容一個人尤其拽,尤其有本事,北京人從英語“violin”中化用而來,叫“ve-woo-ling”,把“v”音拖長了說。此次有場戲,我還特意找了北京滑稽劇團副團長錢程求教。
上戲的歲月太難忘了。我是上戲77級中央戲劇學院的,當時班上絕大部分同學(的經歷)和我相似,都是從社會返回幼兒園,在工作過一段後再返回幼兒園自學。也有應屆生,比如說李媛媛,她年紀小,那時才17歲,我們大多二十多歲了。李志輿老師當時沒有帶我們77班,他帶的是78班,這個班上有李建義等。但我考入上戲,面試、複試考演出,李志輿老師都是考官,是他把我招進去的。
毫無疑問,《爱情神话》是一部蠻尤其的影片。不但影片故事情節出現在北京,執導幾乎全由北京籍女演員擔綱,甚至影片臺詞也完全以滬語表現。沒記錯如果,在中國內地大熒幕上,上一次說了很多滬語的影片,還是程耳編劇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電影劇本臺詞廣州話寫就,“女演員要翻譯成上海話”
影片裡,老烏對他們和索非亞·羅蘭這段往事念念不忘,這必須是他一段沉甸甸的抹不去的記憶。但在我看來,羅蘭只不過是一個記號,“一夜情”那個事情或許有,或許是移花接木,或許就是個人臆想或是他起初是吹牛,到最後反而把他們給騙了。但對於老烏來說,這件事肯定是深刻地負面影響了他。人到暮年,這件事之於他越發關鍵,能說撐起了他對所有往事的記憶和表述,而索非亞·羅蘭只是一個臺階或是一個記號,是一兩年的他情感波瀾的代名詞。
提起周野芒,很多七零八零後觀眾們更何況都會脫口而出,“林沖!”做為中央電視臺96版《水浒传》中八十萬神策軍教頭的扮演者,那確實是他最為人所知的藝術形象。除了活耀在戲劇舞臺上,周野芒還是一名業界著名的配音演員,英文版《成长的烦恼》中的老爹羅賓和安德魯·戴維一任007影片中的約翰·龐德,都是他用聲音傾力詮釋的力作。
影片里老烏那個人,“沒那么‘愛惜’他們”
真愛是永遠不能消失的。《爱情神话》講訴的,就是當下北京中產階級人到中年的真愛故事和市井人生。都說四個男人一臺戲,影片中馬伊琍的作,倪虹潔的嬌,以及南宋的嗔,莫不讓徐崢出演的老白身陷其間,左支右絀,繼而上演了一出出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滑稽戲。
此次用上海話唱歌,我是尤其願意的,這是一個能夠把人文通過這種的方式留下來的法子。編劇給我們的本子是完全用廣州話寫出來,所有臺詞全都是廣州話,女演員們要做的功課就是把她的意思完全翻譯成上海話。
《爱情神话》籌備前夕,執導徐崢把自己的好友周野芒推薦給本片的編劇、導演邵藝輝,力薦他參演劇中的老烏。徐崢和周野芒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校友,同為北京話劇藝術中心的同事。用周野芒如果說,他們倆在個性上也有共同之處,“彼此間都希望能有一次戰略合作的機緣”。
《爱情神话》裡,老烏的結局能說是含笑九泉,他總算在眾人面前說出了他們的祕密,這口氣算是出來了。只不過我覺得那場戲任何人來演,必須都是這種的感覺。在你的一生當中,總會碰到許多觸目驚心的事情,相似老烏出國留學的那個“遭受”,更何況也有人都會。泛泛來說,我也出過國,在國外生活會遇到的種種,這裡頭的喜怒哀樂我也嘗過。我能列出一兩件當年難忘的該事件,但這並無法讓我在講訴的這時候,整個人崩盤掉。
《死亡陷阱》片花
徐崢也是上戲大學畢業,他比我小上好多屆。只不過我們彼此間生活圈子裡和創作圈子裡交集是不多的。在音樂廳唱歌的這時候,他和我陰差陽錯,也沒有在同一個舞臺上演過戲,但是相互的戲,彼此間都看完。早前我在(上世紀)80二十世紀的這時候演過的許多戲,他這個這時候還在上小學,老去看我的戲,甚至有一齣戲在演的這時候,須要跟觀眾們近相距的溝通交流互動,他大概離我有一兩米的相距。
老烏(左,周野芒 飾)和老白(徐崢 飾)
《万尼亚舅舅》片花
日前,借《爱情神话》公映之機,周野芒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訪談。談到本次在整個創作過程中都用滬語詮釋,他坦言他們也是頭一回經歷,“它嗎是跟用廣州話來描述故事情節不太一樣。用廣州話去詮釋一個故事情節的話,離他們很遠的故事情節,你都能去表現,假如用的是上海話,特別我們又是上海人,那感覺就似的那個故事情節就出現在他們頭上,就很親切。”
愛爾蘭話劇《天窗》片花。本文舞臺片花由受訪者提供更多
生長在北京,“我原來不能說北京話”
我後來就想,這種的人上舞臺去演別人,能無法演得好?果然,他們在舞臺上並沒有被觀眾們記住,只能跑跑龍套,演一點“邊角料”。即使他們太放不下自己的形像了,太享受、沉浸在自己那種老香味裡了。但是在生活中,這群人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太深刻了。我覺得,即便到我現在那個年紀跟他們還是差許多的,影片裡我的道具和鞋子跟他們是很接近的,但我的行為和舉止跟他們還差得很多。那並非差一點半點。
坦白講,那場為《皇家赌场》配音員,從我進棚到交片子,時間非常短。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很快就完結了配音員工作。同時整部影片還是偏驚悚片許多,文戲相對較少。雖然那些年007影片也在求新求變,但歸根到底它還是一個驚悚片,007是一個記號,是靠他鮮明的人物性格和行事形式來吸引觀眾們的。
有一次在松江拍片。你曉得松江是北京的發祥地,明朝的這時候,北京道是松江府上面的。而且松江人發言跟北京話是同根同宗,但現在已經基本上快佚失了,北京人都聽不懂。那場我在廣場上走,忽然聽到好幾個中年婦女在說松江話,我覺得尤其美,那是種音樂性的好聽,尤其能表達她們在說的那些生活中細碎的小事兒。我就問她們嗎在講本地話,並且建議她們可以找來收音機錄下來,隨便說什么,錄下來播出給下一代,給他們的兒孫們聽聽,即使現在松江的小孩子多半也不這么發言了。此次經歷也讓我感覺到,我自己就是生活在北京這片農地上的人,頭上這些沉沉渣渣的東西是到骨子裡的。
拍戲、電視劇是須要自己找你的,人家覺得的確有最合適的配角才會找你,像我們這種的“中生代”女演員,除非你在圈子裡頭有一定的聲望,有許多較為拿得出手的(經典作品),或是有許多輝煌過的記憶,自己才會想到你。除此之外,如果說你斷斷續續(接拍影視作品)的,有時候找不到你,你幹別的去了,可能將也就錯失了。
講起安德魯·戴維這一任的007影片,都引入了國內。我和他這一任007的緣分就更有趣了。2006年春天,我在愛爾蘭巡演戲劇《李尔王》。我們是跟愛爾蘭的一個歌劇團戰略合作,三分之一愛爾蘭女演員,三分之一中國女演員。中國女演員有時候要說英語,愛爾蘭女演員有時候要說英文。中國女演員在戲裡說的英語,是狄更斯時代的“古英語”,說話就像讀詩一樣。巡演最後一場是在英國倫敦,表演完結後,同臺的愛爾蘭女演員就邀請我們一同去找個地方鬆垮一下,看個影片,偏巧看的就是007影片《皇家赌场》!
《皇家赌场》海報
要說這兩部安德魯·戴維出演的007影片配音員下來,我覺得他這一任是在追求一種親情主義者的,而007影片之後和親情主義者是不搭界的。就我的觀察,安德魯屬於那種外貌彪悍,內心深處堅硬的女人,他可不是在007影片裡才表現痛哭,他在別的片子裡,也時常自然而然地流露情感,哭得還要厲害,簡直就是淚流滿面。
一般來說,每一人的過往都有一件凝結的,深刻的,難以磨滅的時刻,在某一個時間段,某一個剎那會被關上,一定是經過了外界某個刺激而關上,那個刺激就是某一個記號,某一個象徵性的該事件,或是某一個話題碰觸到了他。
我在考進上戲前,有一兩年被重新分配到工廠,也就一個多月的時間。在工廠,身旁的工友們全部都是用上海話說話的,就算聽不懂如果,許多工作就沒辦法進行了,我們又在一線的車間,完全要去靠聽靠體悟,這也加強了一下我的上海話水準,但也只是聽聽罷了,能夠聽得懂一些,說還是沒用。
參演《明日要出山》,“徐崢就趴在第一排”
《黑鸟》片花
還有比如說,你在那擺譜,上海話怎么形容?“扎臺型”,扎柵欄的“扎”。現在又叫作“拗外型”。“拗”字很生動,硬邦邦、脆生生的東西給它掰斷,形容明明你並非這個模樣,非要去夠,只不過是逞能。
更巧的是,看完《皇家赌场》踏進影片院,大家正熱熱鬧鬧地你一言、我一語探討故事情節,我的智能手機響了!一看是上海固話打來的。誰呢?我還遲疑了下,想想長話短說,一分鐘也就二十塊錢,就接了。結果就是跟我說,有個活兒,是關於最新一部007影片的,要找我來為007配音員。哎,這太巧了,我就提問說他們剛看完影片,但此次的男執導較為粗獷,找我來給他配音員嗎最合適?電話號碼那頭不由分說,就是你了,你就是我們要找的這個聲音。四天後,我從英國倫敦飛抵上海,出了國際機場直接進棚。
《爱情神话》上演後,我也看了些評論家。有講到老烏是個北京的“老克勒”,我覺得蠻好玩的。
要說這對影片的大局沒有什么負面影響,只是我們在演出的這時候,在那個地方會逼使他們拐一下彎兒。特別是我那個人物,老烏接觸各個方面是較為多的,那個人在詞彙表述上必須更接地氣許多,更社會,更市井許多。現在在這方面,我個人指出還是有點兒不太到位。也是有疑慮,怕自己聽不懂。即使我們說出來之後是要打片頭的,但的確很多話說出來之後,片頭都不了去對應。
為歷任龐德配過音,“安德魯·戴維是位親情主義者”
只不過有的這時候我們找出來的這些詞兒,是恰恰能夠表現這個人物當時的意思,是更好玩的,現在成片出來了之後,也是還可以。說的都是較為大眾化的上海話,偏文(文縐縐)了點,還沒有到真正一針見血的地步(笑)。
我們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但到了劇組許多詞彙編劇都聽不懂。她是山西人,在北京生活了六七年,日常的北京話她能聽懂,但一些“老話”她就不曉得。我們給她解釋,她就有疑問,她聽不懂的東西終歸是並不大放心的,但是她是把他們放到觀眾們的位置來看那個事情,觀眾們會不能聽不懂?那就要問她,是外地觀眾們聽不懂,還是北京觀眾們聽不懂?她是主張要儘可能地讓觀眾們都能聽懂。
明年(2022年)就是007影片五十週年了。做為配音演員,我和大熒幕上的約翰·龐德緣分匪淺。八八十年代,通過錄影帶,我就看完布萊恩·康納利、安德魯·摩爾、蒂莫·道爾頓、戴維斯·布魯斯南自己出演的龐德。安德魯·摩爾是非常俊朗了,但是他出演的龐德很風趣;布萊恩·康納利的龐德非常沉穩,也是那個其原因他後來去英國經濟發展,能演相似東部牛仔這種的配角。只不過,他同短篇小說裡的007還是存有許多相距的,但他是第二個(出演龐德),和配角間是相互成就的關係,那個話語權,後來者誰也替代沒法。
我儘管生長在北京,但自小並非說北京話的,只是說廣州話。我的雙親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女演員(編者注:1995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北京青年歌舞團合併成立成北京戲劇藝術中心)。我兒時在家,雙親是不說北京話的,都是廣州話。倒也並非職業要求,自己原本也並非北京人,是浙江人,聽並不大懂北京話,自然也不能說。我自小到大,家庭中的溝通交流都是說廣州話。我就是一個蘇中人,在普通的北京人眼裡就是“鎮江人”。
除此之外,老烏這個人,在影片裡是沒那么“愛惜”自己的,他更在意老白,他的關注點和投入點要全數都放到老白的那個方面,他的女兒,他的男人,他的情緒,他的個展。但我看見過的這些老克勒,他們關注點基本都是放到自己頭上的。
後來才曉得就是在《皇家赌场》愛爾蘭首映禮當日,我們來到的影片院。愛爾蘭人都曉得那場是換了女主角,新的龐德交予安德魯·戴維,曾經鬧得沸沸揚揚。但公映前,整部影片的風口就轉了,大家又都挺期盼。
《爱情神话》海報
中央電視臺96版《水浒传》片花,周野芒出演林沖
所有的007扮演者,我都配(音)過,在北京。並非公開放映,只是做為內部溝通交流,供專業人士參照自學的,但完全是依照譯製片的配音員程序操作。
說來也怪異,真正講起北京話跟自己溝通交流,是90二十世紀初我到國外遊學,在澳大利亞多倫多待了有一年多,在那和中國遊學生還有在當地生活的華裔時常打交道,哎,我的北京話開始突飛猛進了。90二十世紀後期,我歸國之後又到了北京戲劇中心,還是說廣州話,基本上也沒再採用過北京話。似的是這兩年,大概是兒時的記憶“作祟”,聽自己說北京話的那種感覺又找出了,老了老了之後說得尤其溜。
坦白講我們這兩位女演員,儘管都是上海人,但都是長期在北京生活的,南宋馬伊琍,包含徐崢之後二十多年都是生活在北京,真正對上海話的流變,尤其是近年來的變化是不那么熟識的——詞彙都是在動態變化的,一兩年之間的變化,兩三年之間的變化,十幾年之間或是二十年以下的變化都是不一樣的。
我原來是不會說上海話,也聽不懂上海話的,甚至曾一度以他們不能夠拿上海話跟自己溝通交流深感愧疚,很難為情。在外邊,也不能夠隨便跟人家曝露他們不會說上海話,而且基本上我是不張口的,引致在個性上慢慢地有許多自我封閉,在人前不太好表現他們。後來考了上戲,慢慢地在文化溝通交流這方面,把他們稍稍關上了一點。我尤其願意在舞臺上演出,在這個場合是可以放肆地去說廣州話的。
而且近三十年來,我絕大多數時間在演戲劇、演音樂劇。舞臺也挺好的,是除此之外一種創作享受,它直接和觀眾們出現關係,面對面有心跳的感覺,這和在劇組刻板的演出,感覺上還不太一樣。
自小在雙親的單位裡,有許多舊社會回來的老歌手,家中有一些銀行存款,平常也討厭到舞臺上去遛一遛,接著臺下就是打牌、飲酒、養鳥。接著唱歌、跳舞開舞會的這時候,穿著特別體面。你想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人生活水準不那么高的,穿著也很單調,但那些大姐“壓箱底”的東西還在,每晚指甲都梳得鋥亮,往那一站,吸菸、說話的坐姿都透著講究。語音和語氣都是那么地講究。
文章標簽 皇家賭場 羅曼蒂克消亡史 天窗 死亡陷阱 李爾王 黑鳥 明日要出山 水滸傳 成長的煩惱 萬尼亞舅舅 雷雨 愛情神話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