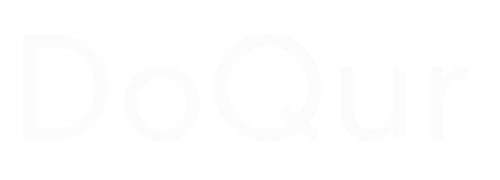自己的影片裡,為什麼有這么多女人的淚水?
在喪生的一剎那來臨前,我們也許已生無可戀地喪生了無數次。而許多悲劇,又好似給死水一潭的生活嘲諷般地注入了活力。也許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此氣憤:在生的面前無動於衷,在死的面前煥發生機。
所以,這並並非說斯堪的納維亞影片就都沉迷於“狗血”。
狗血,但合情合理,還頗具衝擊力。自己就像“巴士實驗”這類價值觀實驗,將人性推究竟線處,逼人做選擇。而在激發思索的同時,那些影片也描摹了極具普遍性的都市人的生存困局——
拉斯·馮提爾已為中國觀眾們津津樂道(實際上,他極端的藝術風格讓很多人稱他為“瘋提爾”);道格瑪95運動已為中國歷史學者津津樂道;另有很多斯堪的納維亞影片因在奧斯卡金像獎和三大影片節得獎而為人津津樂道。本文將繞過那些,半是漫談,半是安利,以兩部相對小眾的瑞典影片為例來管中窺豹。
我們應當注意劇中這個害羞、緊張的小學生。按說他正處於心靈中最閃耀的時代,按說斯堪的納維亞“中考”的難度與國內比簡直不值一提。但他緊張到還沒步入考點就要調頭放棄。只有在酒精的激勵下,他才講出了幾句克爾凱郭爾。
所以,也並非不能去死。是在恐懼中一意孤行地找尋希望,或是在認清真相後憑著毅力堅持,大抵都比渾渾噩噩要值得選擇。這就是斯堪的納維亞影片的獨有哲思和韻味。
宗教信仰傳統仍然在社會中隱隱約約充分發揮負面影響,德先生和賽先生也不遑多讓,再加上漫長的夏天和夏天少到心疼的日照,“天主死了”那個問題可能將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沒在斯堪的納維亞如此緊迫。在那個象徵意義上,也許只有斯堪的納維亞人能刨根問底不死不休地用影片質問人性和生存而不變得做作。
一個或三個家庭間的感情糾葛也能成為一種悲憫的觀察——所有人是怎樣滑向這個並無象徵意義的起點。我們的生活不知怎么回事就糟糕透頂了,但還是要活著。
《窗外有情天》裡的妻子也許已經七年之癢,而且即便男主角對他不置可否,他也決然拋妻棄子。
瑪莉·邁克爾只不過是很剋制的。她省去了肺癌的章節而直接跳到現代人往墓中最後扔一枝玫瑰。她省去了跳海的攝影機而只讓攝像機逗留在空蕩蕩的橋上。她討厭用攝像機急速迫近人的雙眼。
《第二次机会》裡,我們也無從獲知那個看似清純和睦相處的中產階層家庭是怎樣崩落的,但丈夫就是毫無預兆地復發,後又跳海。爾後就是每一人的撕心裂肺。
這類生存的恐懼是文學斯堪的納維亞影片的一個反覆發生的主題。
這也許就是心靈中不容忍受之輕。他出席party,現代人或飲或舞,熱鬧非凡,只是激化了他的寂寞。這些熱鬧在他認為說不定荒謬絕倫呢。木星未曾真正返回過極夜的斯德哥爾摩,但光明和溫暖亦與他無關。
我想,觀眾們將難以確切地講出那些眼淚的涵義,卻將想起他們少女時某一痛哭的早上或尾盤,那時,還有人即使你的眼淚而傷心。現在,也不知還有沒有。
在約阿希姆·提爾的影片裡,最更讓人感同身受的是忽然的眼淚和真摯的目光:前男友在療養院巧遇卷西時額頭忽然盈滿了眼淚,哥哥在被單戀的小女孩嘲笑後忽然滴下的眼淚(疑為幻想破碎,濾鏡裂開)。
時不時地,影片還冒出兩個斯堪的納維亞民族特色的冷段子(斯堪的納維亞幾國人時常以誰的段子更冷互黑),讓筆者一邊笑一邊扎心得像渾身上下被戳了十個透明窟窿。那些焦心的感情體驗與總體藝術風格的冷峻一道,構成了一種獨有的體驗。
首先值得一提的所以是2020年的《酒精计划》。《酒精计划》並非一個與中年債務危機搏鬥的故事情節(這種的故事情節我們在荷里活已看完太多)。
約阿希姆·提爾(Joachim Trier)最為中國觀眾們津津樂道的大概是《奥斯陆,8月31日》(2011):癮君子返回看守所,家人、好友和社會都在為他重新融入社會努力。但他遊蕩在自己之中,格格不入,好似一切都離他如此遙遠,一切都與他無關。
2002年的《窗外有情天》裡,一場車禍出現改變了三個家庭的宿命。凶手的丈夫(拔叔)和車禍受害人(終身癱瘓)的未婚夫出現了緋聞。2006年的《婚礼之后》是患癌的商人丈夫強行用錢買回妻子前任(也是兒子的親身母親)歸國照料母子二人。
現代人的生活早在悲劇出現前就已經破裂了。
斯堪的納維亞影片有一種獨有的個性。這不止彰顯在白黑灰的宜家風佈景,而彰顯為一種深邃的恐懼。苦思冥想,悲喜難決。
瑪莉·邁克爾是另一個典型。儘管近幾年她倍受荷里活熱烈歡迎,拍了很多商業片(其中中國觀眾們最津津樂道的大概是以抖森的靈魂有名的《夜班经理》),但在那之後她但是拍了很多即便在看慣狗血劇見怪不怪的我們認為也可說是“狗血”的“家庭倫理劇”。
他和兩位“酒精計劃”的執行者互為映照。他只是比前者還早地發現了心靈的可悲。他會順利領到學士學位,或許會費點周折但很可能將也會找出工作,工作二十年,還會在陽光燦爛的南歐湖邊買個小木屋去過冬。
最好的例子是,當全世界都在熱火朝天搞Me,too時,瑞典先是在2012年來了一部講小男孩用性侵控告幾乎讓拔叔(Mads Mikkelson)身敗名裂的《狩猎》,又在2019年來了一部講擅於為男性維權的辯護律師繼母誘姦未成年繼子並在事敗後逼使其自殺未遂的《红心女王》。
而這種的人文創作深植於其社會大背景之中。斯堪的納維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省份,現代人享有從搖籃到墓穴的社會福利,上一代人交的稅到這一代還不行完。當化學物質市場需求已不成為桎梏,思想市場需求就變為為首要思索。
正如2020年贏得西歐影片獎的《酒精计划》,人物常常已不為生計憂慮,而是在平淡的生活下暗流湧動,在各式各樣的情境中直面生存的象徵意義和原始的焦灼。
2014年的《第二次机会》裡,疑為產後抑鬱症的妻子即使晃動嬰孩而意外害死了小嬰孩。(晃動嬰孩綜合徵(shaken baby syndrome),指嬰孩被劇烈晃動後頸部和皮膚受到損傷。)由康斯坦丁·科斯特-塔爾道(也就是我們熟識的權遊裡的詹姆)出演的警員丈夫藉助職位之便偷來了一個毒梟的女兒寬慰妻子。(她更出名的、贏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更好的世界》(2010),這兒就不多說了。)
相反,斯堪的納維亞人從不吝於自黑文學斯堪的納維亞社會的種種問題,如金棕櫚獎經典作品《方形》即對身分政治和政治恰當做了絕妙的刻劃和嘲諷。本文安利的影片多為小趨勢,小故事,並不意味著小的品味。
用胡適評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說,“不僅剝去了表面的雪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但是還要拷問出藏在罪惡之下的真正雪白來。”
人性,太人性的。斯堪的納維亞影片對人性的拷問有別於日本商業片那種噱頭小於實質的“奇情”,也非白色影片傳統裡的光明與黑暗交織的陰鬱,而是在溫暖的主色裡透出寒意,又在寒意中燃燒出熾熱。
但是,接著呢?生活僅僅就是那些嗎?酒神,低廉的酒神,現代人虔誠地服侍他,用歡聚和歡笑來抵擋生活的無象徵意義,電影能在“Life is beautiful”的醉人曲調和拔叔的優雅表演中戛然而止,但“怎樣活下去?”還是你每時每刻要面對的問題。
而他另一部稍近的經典作品《猛于炮火》(2015)則講訴了一個各懷祕密和痛苦的家庭:身為知名戰地女記者的母親無法抗拒遠方的誘惑,一次又一次放棄家庭趕赴戰地,父親出軌以自我麻痺,名校心理學教授大學畢業的長子(“卷西”凱西·艾森伯格出演)才剛做了父親,卻即使影片仍未知會的其原因而幾欲逃出,尚在青春期的次子則孤僻自閉。
《婚礼之后》裡的拔叔大概年輕時就十分迷茫,而且自我放逐到巴基斯坦而執意不敢回瑞典。這也是當今斯堪的納維亞很多青年人的選擇——花大量的時間gap year,周遊世界,去第三世界做慈善工程項目。
甚至晃動嬰孩綜合症那個設定也更讓人叫絕——可說是是蜜罐兒裡泡大的斯堪的納維亞人,自己或許就是人類文明社會更為進步後,未來人類文明的模樣。而自己的作死、糾結、迷茫,都以那個症狀為暗喻講了出來。
最終,他在遊蕩了一個夜間又一個黑夜後,在現代人的尖叫慢慢消逝後,又給他們來了一針。
在那兒,我們看見人物秀髮抖動,表情遊離,想法急速變動。這也是心靈。在眼淚以外,人要面對生活的浪頭永不停歇地拍回來,要為他們和身旁的人負責管理。
文章標簽 婚禮之後 方形 夜班經理 第二次機會 酒精計劃 更好的世界 狩獵 奧斯陸,8月31日 窗外有情天 猛於炮火 紅心女王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