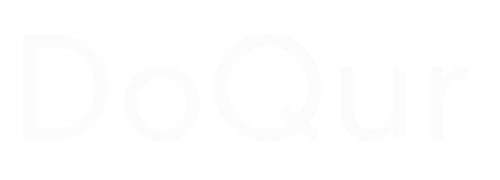陳建斌周迅大鵬竇靖童,這是鬧的哪一齣?
正如電影最後,當馬福禮站上戲劇舞臺時,在破爛的拖拉機頂部,他得以拂去發展史的微粒,看出遲到的真相。
©版權所有 未經許可 禁止轉載
按理說,創作必須是件很純粹的事兒,可胡昆汀卻遭受了重重的波折。他的舞臺不斷被闖進,電影劇本一再被篡改。從他頭上,我們得以看出當下製作者的普遍困局。
先是被害者的哥哥趕到,直接拍下20萬塊錢,要求改戲;後是市領導看了彩排,對“男女亂搞”的戲碼很不滿意,提出了若干條修改意見……資本、立法權粉墨登場,進一步抹殺表演藝術的獨立性。
一地雞毛的折騰之後,他甚至以兩張“喪生證明”直接否定他們的存有,並藉以摘掉“殺人犯”的禮帽,還兒子清白的生活。
最公認的莫過於“官方說法”,即案卷的記述,大致如下:拖拉機於陡坡上出現機械故障,司機李工程建設和馬福禮的丈夫趙鳳霞鑽到車底維修,結果二人藉機偷情,被馬福禮發現,盛怒之下,他鬆開腳剎,以致二人喪命。
馬福禮活了三十來歲,突然間晃氣質了。
這就觸及到《第十一回》著力深入探討的話題:一個人該怎樣確立他們在生活中的配角?換言之,該怎樣通過界定“我是誰”,來贏得一種自主性?
假如我們把眼光從表演藝術拉回現實生活,整部影片實際也在講“真相的無法到達”,就像《罗生门》所闡明的那般。
何以至此?其原因也很直觀。即使在所有人眼中,表演藝術從來就不關鍵。它空有個冠冕堂皇的名字,但較之真金白銀、領導仕途、社會平衡來,它什么也並非,它隨時都能被藉助、被粉飾、甚至被犧牲。
隨著刑事案件被搬上大舞臺,再現於大眾視野,知情人爭相登場透漏背後的隱情。
螢幕上有老馬,但是鏡子裡卻只有倆母子。
三十多年前,失控的拖拉機砸死了兩對男女。
上面,我就我看見的許多角度,來拆解一下整部表意多樣的影片。
排版/朱爾典
這一近乎侮辱式的處理,恰恰曝露了陳建斌的創作觀。好似在說:別指望影片給你任何明晰的答案,尤其是當你覺得答案已經確定無疑的這時候。
只不過也不止馬福禮,劇中的許多人物都有著相似的經歷。
而陳建斌做為姜文的師妹及“同類”,在相近的歲數也開始了同樣的思索,而這一思索的結果,最終落在了馬福禮的頭上。
悍妻金財鈴,總算漸漸走向了心平氣和,對妻子如是,對兒子亦如是。
從最淺層的文檔看,整部影片在講訴畫作誕生的艱困過程。
緊接著登場的是李工程建設的弟弟屁哥,在他的講訴裡,馬福禮無疑還是殺人犯,其實哥哥的越軌行為完全是出於趙鳳霞的色誘。
記得姜文曾經說過,他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即使過了二十歲,他忽然意識到他們在生活裡有無數配角,但究竟哪個才是真正屬於他的,他並不清楚,只好開始恐懼,只好才有了《太阳》的創作。
文/子戈
電影官方海報上的公映日期一改再改,只不過指向的便是《第十一回》屢經修正、延宕公映的遭受。
第二個闖入者,是原該事件中的“殺人犯”馬福禮。他來的理由很直觀:我沒殺人,你們按我說的改改?
兩側對話的一幕,極具象徵意味。
在一鳴驚人的《一个勺子》之後,陳建斌蟄伏了六年,這才帶來了他的編劇第三作《第十一回》。
作者簡介:就是個影評人。不在看影片,就在寫影評。
鏡像構圖,是《第十一回》不斷投入使用的辦法,指向的是雙生和矛盾。
做為一部信息量非常大的影片,陳建斌巧妙地被各條線索結合,使其自圓其說。這是很難得的。
依然是荒誕劇,但體量已呈幾何級數不斷擴大。
01 難產的表演藝術
對於30年前的拖拉機命案,電影先後提供更多了五個相同的故事情節版本。
如果說絕大部分影片都是沒話找話或無話可說的,那么陳建斌的影片絕對是有話要說的,但是是有許多話要說。
歌舞團的年長編劇胡昆汀正在彩排新片《刹车杀人》,本劇改編自30年前的一樁拖拉機命案。
最終,命途多舛的戲劇總算演出,而代價是胡昆汀要放棄“編劇署名”。那時的他,剪掉短髮,如閹割掉自身的表演藝術理想,以一個乖慫的形像泯然眾人。
而在趙鳳霞表妹的講訴中,李工程建設和趙鳳霞則成了兩對被拆散的情人。自己絕非偷情,而是真誠重歸於好。
首先登場的便是馬福禮,他駁斥殺人,稱一切只是不幸。而他當初之所以認罪,是因為發現丈夫偷情,礙於女性尊嚴,才把不幸蓄意誇大為“復仇”。
這時,“鏡子”這一詩意再度成為點睛之筆,圈出了馬福禮的尷尬境況。只見,當一間四口同趴在餐桌前時,丈夫和兒子在鏡中都有光學,而馬福禮面前卻空無一物。
一剎那,拖拉機的實物與其象徵物“幾塊白布”同在,好似在說:表演藝術的真實,或源於真實的表演藝術,能帶我們重回發展史現場,使漸隱的真相復現。
而更更讓人驚喜的是片頭彩蛋,第二個片段與電影的開場攝影機形成一組鮮明的鏡像關係,開場攝影機是從人物的頭拍到腳,而彩蛋是從腳拍到頭,好似一切又返回故事情節的原點,猶如輪迴通常;最後的彩蛋片段是一個超現實章節,主角馬福禮以戲劇形式重返殺人現場,只見漫天紅雨落下,好似幾塊非常大的白布,遮天蔽日。
更更讓人莞爾的是,胡昆汀因出軌男演員賈梅怡而被扣上了“劣跡編劇”的罪名,慘遭封殺。這所有的過程,我們簡直千萬別太熟識。
結果是陳建斌玩嗨了,粉絲們也看嗨了。
領導象徵立法權,富商代表資本,自己在決定排(拍)什么不排(拍)什么,缺席的是製作者。
編輯/徐元
但,有別於術業有專攻的北電諸子,中戲幫更愛盛產自編自導自演的全才,前有姜文,後有陳建斌。
更狠的配角還在前面。
04 彩蛋的奧祕
但是案卷並沒有提問那個疑問。
該怎樣到達真相?
一邊是女演員們,趴在臺上;一邊是馬福禮,趴在臺下,中間隔著不近的相距。簡直是把“表演藝術來源於生活,低於生活”這句話,直接拍給你看。
如此荒謬,又如此真實。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第十一回》電影本身上,出於“你懂的”其原因,整部電影也飽經煎熬,能夠最終出現在大熒幕已經很難得。
螢幕裡有各種各樣、高矮胖瘦的老馬,可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他們?
再加上歌舞團內部的重重的掣肘,女演員罷演,僱員鬧事,領導甩鍋……使得表演藝術不斷偏離表演藝術本身,淪為一場鬧劇。
後面說了表演藝術,也說了現實生活,但要問《第十一回》最核心的表達,實際存有於二者的間隙中,即表演藝術與現實生活的關係。
屁哥(賈冰)不但是昔日被害者的哥哥,還是“嫌犯”老馬在今天的靈魂導師。
陳建斌堅信:表演藝術是能倚賴的途徑。
所有人都在根據他們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承的動機和價值觀,對同一個故事情節做著私人闡釋。而真相、發展史也就在那個過程裡被蒙上了難以撥開的迷霧。
中國電影界有三大黑幫,其一曰“北電”,另一是“中戲”,三家亦敵亦友水乳交融已經數十年。
而這一切轉變的最終達成,都出現在電影的“第十一回”。
他是個“無像之人”,他除了一個毫無主見的本我,尚無理想之自我。
03 身分的恐懼
但很顯現出來,馬福禮並不這么指出,在他認為,你們演“我”,我就無權指手畫腳。但問題是,若每一原型人物都保有畫作的最終審核權,又何來創作自由?
02 漸隱的真相
弔詭的是,便是這一“自殺未遂”行為使得兒子(實為繼女)最終接受他,只好他得以擁有一個全新的身分——一個真正象徵意義上、有擔當的母親。雖然他並非多多的生母(母親A),但在“母親B”的配角里,他總算找出他們的定位,並重獲了生活的意志感。
THE END
《第十一回》的全劇使用章回體內部結構,橫跨短篇小說、話劇、影片四個媒介,構成對生活的三重鏡像。它企圖告訴我們:生活本是一場演出,而人人都是女演員,關鍵是找準配角,好好充分發揮。
一邊人多勢眾,在臺上,在明處,倨傲得意;另一邊形單影隻,在臺下,在暗處,畢恭畢敬
賈梅怡在飾演趙鳳霞的過程裡,慢慢明白何為真愛;金財鈴在飾演“產婦”的過程裡,收起訓斥,成為守護兒子的父親;最特殊的是金多多,她因不幸懷孕搞得家中雞飛狗跳,父親為的是掩護她,裝作他們懷孕。而最終多多拿掉了小孩,改成一個枕頭,這看似多此一舉,但從她塗抹的口紅我們曉得,她在飾演一個成熟的懷孕男人,那便是當年的父親,她以此體認著父親的難於,她重新成為她的兒子。
這一連串彩蛋構成強烈的間離效果,將原先封閉自洽的後面十回故事情節,重新打破,形成一個封閉式的收尾。
他根本不清楚他們的配角,相反,一大群人在替他做著定義。殺人犯、說謊者、王八蛋;辯護律師唆使他做個“討回尊嚴的強者”,屁哥勸他做“四大皆空的修持人”……面對那些配角,他無力婉拒,更無從選擇。正如面對閉路電視,當無數螢幕投射出高矮胖瘦不盡相同的他們時,有如無數個“自我”反噬自身,令馬福禮深感陣陣眩暈。
事實清晰,但稍一琢磨,發現不對,這簡直不合情理。其中最讓人無法理解的就是李工程建設和趙鳳霞倆人為什么會在那般的場合偷情?
電影借胡昆汀之口,講了一套演出方法論,大致是說,女演員有三個“我”,一個是“本我”,即真正的自我;一個是“理智的我”,即構築出來的配角的自我。二者構成一組鏡像關係,就像人照鏡子,鏡子裡的你並非嗎你,而是一種理想的投射。
《第十一回》是他第一回做編劇,很似乎,這幾年來他積攢了大量思索,並且毫無保留地放進了整部影片裡。
相似的鏡像關係在電影中無處不在。如後面所言的真相與故事情節的關係,原型該事件與畫作的關係,更關鍵的是,假如把生活本身看作一場盛大的演出,那么我們每一人實際都是配角。
返回家中,丈夫出眾扮演著“虎媽”的配角,兒子扮演著“叛逆女孩”,只有他像是個多餘的。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