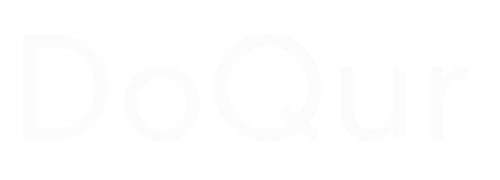王家衛是怎樣讓《重庆森林》成為後現代主義影片實踐樣板的?
張學友:不曉得。想起來再告訴你。
劇名中的“武漢森林”指的是一處坐落於銅鑼灣(第二個故事情節的主要外景地)的建築物,這兒充斥著各式各樣小生意和犯罪活動,遍及為旅行者和揹包客所津津樂道的低成本旅店。英語劇名“Chungking Express”的其它涵義我會在下文詳細描述,但它也起到了將電影隔開為幾段的促進作用:“Chungking”指的是以武漢大樓為主要大背景的第一段故事情節,“Express”指的是以“晚上特快”(Midnight Express)為中心的第二段故事情節,“晚上特快”是坐落於尖沙咀蘭桂坊的一個知名餐廳,可從銅鑼灣搭乘渡船沿著維港抵達。
因而,與之相應,《重庆森林》亦可被敘述為一部實驗性的高速公路片,其實驗性被影片的藝術風格(倚賴記錄片畫法,比如拿著攝影、光線、攝影機內效果)和不連貫的敘事所確認,給觀賞者製造出一種迷失感。只是由王家衛電影所引致的此種迷失,來自諾埃爾·伯奇(Noël Burch)在《电影实践理论》(Theory of Film Practice,以法語初版於1969年)中的闡釋,此書預測,分攝影機(découpage)“從把敘事水解為場景的侷限象徵意義而言,對真正的製作者不再有什么象徵意義……將不再逗留在實驗性和純理論的階段,而是在實際的電影實踐中贏得獨立”,這時將會“形成未來電影的實質”。
在《重庆森林》中,時間受限於變化,與人的心靈密切相關:到5月1日,金城武就會年輕兩歲;在當天,林青霞也許會死去。這就是時間。在“晚上特快”,時間也會推移,這彰顯在張學友的T恤的變化。該處,時間就是這種穿在頭上的東西。做為一部對時間進行封裝、量化和物化的電影,《重庆森林》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也達至過期的臨界點。它將成為下一代“讀夢人”所“閱讀”的那具骨頭,屆時記憶會再度浮現。《重庆森林》是一部關於時間的電影,它就是時空本身,有如穿在頭上的某物(就像張學友的T恤)——到目前為止都還合體。
郭富城:你討厭聽這么吵的音樂創作啊?
與結城春樹一樣,王家衛為日常生活注入充滿著魔力的元素,但帶著致命感。他和結城一樣,討厭初始化盛行人文的記號來暗示記憶所扮演的配角。林青霞出演的男子戴著假髮和墨鏡,這就是有意識地特別強調她做為影片歌手的形像,林在1970二十世紀便享譽電影界,當時王家衛不過十多歲,可能將剛念初中。在職業生涯的晚期,林青霞時常出演的配角是將要邁入成年的清純女孩。在《重庆森林》中,林青霞的熒幕形像讓人想起結城春樹的另一則短篇小說《1963/1982年的伊帕内玛姑娘》中的人物。
王家衛的空間絕非永恆不變,毋寧說它澄清著這種神學和社會學關於時間其本質的表述,威廉·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提出的“綿延”(durée)正是對此最好的界定。在一個層面上講,“綿延”指的是時間的推移和延續;在另一個層面上講,它指的是同意識和記憶有關的時間。“綿延”是活的時間,即各式各樣排列方式的人類文明實戰經驗。存有著漸漸演化出外部空間的內在的或人的“綿延”,接著它就變為記憶的液體。從整部電影上看,“綿延”有如一曲抽象化運動(時間)與空間共舞的探戈。空間自身只能通過被人居於其間而贏得完整性。武漢大樓就是記憶的虛擬維度,其空間就是一個生動的被時間所填充的(因而也是人的和心理的)實體。
《重庆森林》中何志武的鳳梨罐頭。
實際上,《重庆森林》一開場,就以一位冒牌金髮女郎(林青霞)步入虛幻速率的運動-圖像。速率和運動構成了武漢大樓章節的基調,在那場戲中,林青霞拼湊了一班菲律賓人替她運毒。那些場景合乎快速大力推進敘事的要求,並且處理得非常清楚,劉偉強像印象派畫家一樣令其圖像的表面支離破碎,只好就加強了這種一種價值觀:許多事情在同時出現。打個比方,就像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1912),林青霞的配角擁有雙重皮膚部位。她慌手忙腳地組織運毒犯罪團伙,但被人出賣,一心想著復仇。印象派音樂家聲稱的“運動和光炸燬了粒子的物質性”,在劉偉強的創作中獲得極佳的展現出。
切至郭富城手的特寫,示意她湊近些。跳切至自己側臉的特寫,分別從左右兩邊入畫。他小聲說道:“大廚沙拉。”切至中景(和前面的攝影機一樣),張學友語帶沮喪地叫了一聲,接著郭富城帶著大廚沙拉走開。在那個動態攝製的場景之後,攝影機依然停在張學友這兒,隨著音樂創作搖晃。音樂創作和圖像的流動忽然被跳切打斷,現在我們看見,張學友穿著一件薄荷綠的短袖外套,繫著圍裙。畫外音樂創作仍是《加州梦》,但時間似乎已經變了,空間也轉為張學友的近景,她在櫃檯後面跟著音樂創作起舞,拿著調料的雙腳上下搖擺。老闆娘出來後,她才來到浴室。老闆娘關掉收音機,攝影機切至走向前來的郭富城,他又點了一份大廚沙拉。
我在上文所探討的攝影機序列,可說是文學影片中對影片技巧運用得最為出眾的樣板之一,即使王家衛完美地把握了“綿延”:時空的偶合,同時呈現出了與巧遇和人物關係變化有關的象徵意義與獨到的細微差別。王家衛也許從村上春樹的經典作品中贏得靈感,但不容高估他將各式各樣可能將的負面影響源重新吸納進他那由時空和記憶組合的獨有甜品的技巧。除此之外,王家衛再度展現了他是多么傑出的一名擅於指導女演員的編劇。三位執導的演出可說是典範,恰到好處地表現了人物的哀傷和乖僻。林青霞給出了只有她就可以做到的“空白臉”演出;郭富城的演出更讓人眼前一亮,他即便穿汗衫和平角長褲,也和穿制服一樣帥(他因參演那個配角而榮獲1995年香港影片金像獎最佳男女演員獎,可謂實至名歸)。
《重庆森林》彰顯了此種實際的電影實踐,影片方式上的自主被編劇有機地運用,以展現伯奇所言的“一部影片的時空表達及其敘事內容、方式內部結構(方式內部結構決定敘事內部結構,反之亦然)之間的一致關係”。
郭富城喝咖啡的這時候,王家衛將鏡頭切至兩架直升機在夜幕中降落的畫面,畫外是郭富城的聲音:“每兩架直升機下面,一定有一個空中小姐是你想‘泡’的。今年的這個這時候,我很成功地在五萬尺的高空‘泡’上一個。”在郭富城的閃回鏡頭中,我們置身於他的別墅:他在發展前景中躺在床邊,擺弄一個玩偶直升機,而那個身著內衣和上衣的空中小姐(周嘉玲飾)則站在浴室大門口,啜飲一瓶啤酒;畫外音樂是黛娜·哥倫比亞特區唱的《一日之别》。空間同樣出現了發生改變。郭富城用手上的玩偶直升機去碰觸周嘉玲,在潛意識的真愛前戲中,拿著攝像機追隨這對戀人,從別墅的一個空間到另一個空間,以傾斜的角度從左搖到右,再從右搖到左,模仿著在五萬尺高空出現的誘使。當郭富城把周嘉玲逼到牆角,並送上擁吻時,攝像機暗示了後景中的一個空間:中半山的電動電梯藉由玻璃窗隱約可見,位置比別墅內的床稍高。在這個閃回場景的開頭,郭富城和周嘉玲躺在床邊,他操縱那架玩偶直升機“跌落”在周嘉玲赤裸的脊背上。
切至郭富城側臉的特寫:
郭富城:那你討厭什么?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馬來]張長興 著,蘇濤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
《重庆森林》中的拿著攝影。
那場戲的空間偶合敘述了張學友的恐慌:她正在擦另一面地板牆,藉由它,我們能看見站在櫃檯旁邊的郭富城模糊不清的影子,她小心地衝洗著地板(或郭富城的影子)。鏡頭轉換,焦點對準郭富城,從地板牆後面攝製他。再切至張學友,她還在擦地板,但此次是在浴室通道前面,並且穿了一件帶斑點的白T恤;我們從張學友的視點出發,藉由通道看郭富城,雖然張學友事實上是面對攝像機的——那個出現在不平衡空間中的重複性動作充滿活力,而張學友擦洗、清潔時不斷重複的節拍更加強了空間的不平衡。在相同的時間裡,空間也出現了變化。吉爾·德勒茲說:“心是重複的情慾器官。”出現在那個章節中的重複,可以從社會學和差別的其它維度加以區別。我們現在曉得,郭富城被男友捨棄了,他說:“既然消夜都有那么多選擇,更何況女朋友。好好的大廚沙拉,換什么炸魚薯條?”張學友或許忙於清潔,但她卻偷聽了二人的對話。郭富城看起來略顯哀傷,他只點了一碗咖啡。
我們須要再度提到王家衛團隊(美術指導張叔平,他在該片中出任剪接指導,大概即使譚家明正忙於《东邪西毒》的剪接,以及攝影指導杜可風)的重大貢獻。事實上,王家衛在攝製《重庆森林》的過程中聘用了三位攝影指導:劉偉強負責管理攝製第一段故事情節,杜可風則是第二段故事情節的掌鏡者。打下電影總體基調的只但是劉偉強。比如,王家衛重拾《旺角卡门》(亦由劉偉強出任攝影)的美感構成,在攝製武漢大樓的內景時主要採用紅色,在攝製酒吧時則使用金白色。但,這兒的重要是運動和速率,這一效果的達成,全賴劉偉強那更讓人眼前一亮的手提攝影,杜可風在第二段故事情節中沿用了這一表演藝術風格。劉偉強和杜可風將美感降到最高,並聚焦於布光和運動,自己在電影中所釋放的熱量,便是未來派音樂家在1910年的宣言中所稱的表演藝術的目標。表演藝術評論家托馬斯·裡德(Herbert Read)也闡述過這一目標:
時間和空間或許互相矛盾,但事實上,這些曲目、武漢大樓中充斥著的外語,以及外景地的地理位置(銅鑼灣和尖沙咀),共同促進作用於一個單純的方式層面,它有如一個文檔,令不相干的個體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總體。英語劇名“Chungking Express”有意混為一談空間,給人導致這種一種假象,即銅鑼灣和尖沙咀是一個單獨的、完整的衛星城。電影在世界範圍內一炮而紅,暗示了這種一個事實:這些未曾到過澳門的觀眾們,亦能合乎情理地被電影對時空的操弄視作王家衛後現代主義藝術風格的不可分割的元素。不過,電影的國際軟件包與澳門版有所不同。
《重庆森林》片花。
在張學友身著帶白色心形花紋的白T恤的同一個場景中,與章節開始時的介紹性攝影機一樣,郭富城快步走向攝像機,直接摘下禮帽——那個重複即使張學友的穿著和郭富城所點的外賣而與之後有所不同:這一次郭富城點了炸魚薯條,而非大廚沙拉(他聽從老闆娘的建議,給原先討厭大廚沙拉的男朋友更多選擇)。那個場景重複了郭富城及張學友巧遇的實質。這是從張學友的主觀視點攝製的。實際上,整個攝影機序列不但通過張學友的穿著標出時間的推移,也完全是從她的視角進行觀看的。當郭富城快步走向攝像機,他英俊的面容讓人耳目一新,觀賞者則被放到張學友的位置上:我們的心和她一同興奮,我們幻想她所幻想的,我們和她一樣,為郭富城改點炸魚薯條而深感恐懼和疑惑。
(張學友和著音樂創作的節拍搖搖頭。)
《重庆森林》中破碎的圖像,就如印象派音樂家的藝術風格
有別於之前的《阿飞正传》和之後的《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絕非一部二十世紀劇,亦有別於《旺角卡门》,它不落成規的窠臼,既非一部文學黑幫片,也非一部文學劇情片。在類別內容方面,《重庆森林》的象徵意義更為關鍵:它標誌著王家衛在類別中締造各式各樣變化的信心日漸進一步增強,而這一點恰是他從一開始就孜孜以求的。電影講訴了三個互相獨立的故事情節,雖然王家衛插入了兩個在三個故事情節上均有現身的小角色。
《重庆森林》中的時空偶合的編排,成為了後現代主義影片實踐的樣板
王家衛再度運用他在《阿飞正传》中經濟發展出的關於時間的母題,他將攝影機切至一頭鐘錶,當時間變為早上9:00時,下面顯示的日期為4月28日,星期四。“57半小時後,我會愛上那個男人。”金城武出演的害著相思病的警員以第三人稱獨白的方式(現如今這已成為王家衛的標籤 )喃喃地追憶,但這也許也是村上春樹短篇小說中第三人稱描述的延續。因而,村上春樹對王家衛的負面影響彰顯在兩方面:首先,王家衛的獨白反映了村上春樹短篇小說的對話藝術風格;其二,敘事是對記憶的重述。
王家衛攝製《重庆森林》的首要靈感來自韓國短篇小說家村上春樹的一則名為《在一个美妙的四月春晨,遇见100%完美女孩》的長篇短篇小說。這篇短篇小說表現的是感覺的難以捉摸,開篇第一句就是:“一個奇妙的三月春晨,在大阪原宿風尚區的兩條窄小的馬路上,我與一名100%完美的男孩失之交臂。”與此相近,《重庆森林》也以一場遇見開始,這也成為第二段故事情節的母題:在武漢大樓的一場典型的警匪追逐之後,金城武出演的警員何志武與林青霞出演的長髮男子擦肩而過。
張學友:偷走還是在那兒吃?
《伊帕内玛姑娘》(‘The Gril from Ipanema’)這首在1960二十世紀紅極一時的曲目,首先讓主角想到了初中幼兒園的走廊,從而又讓他想到了包含“生菜、蕃茄、小青瓜、青蜂蜜、蘆筍、切開圓盤圈的洋蔥,還有紫色的千島沙拉醬”的綜合沙拉,那些又讓他想起了從前認識的一個男孩,“她被封閉在第一印象之中,靜靜地漂浮在時光之海里”。
攝製《重庆森林》讓王家衛重返年長時代
如前所述,英語劇名“Chungking Express”也代表著銅鑼灣和尖沙咀——空間地理的集合體,時間和記憶在此通過——三個王家衛一直想拍進影片的地點。在尖沙咀,去除“晚上特快”那個地點,王家衛還聚焦於從閣麟街到中半山加裝自動樓梯的地區。武漢大樓便是銅鑼灣的縮影。王家衛成長於銅鑼灣,對這兒極為熟識:“這兒華洋混居,有著澳門社會最突出的特徵。”武漢大樓代表著澳門多元人文的面向,可說是一個充斥著異域聲音和詞彙的地球村,在王家衛眼裡,這兒是真正的澳門的象徵。“綿延”的概念呈現出在多元人文的人類文明實戰經驗(彰顯為武漢大樓的空間維度)的現實生活中。
郭富城:偷走。新來的?沒見過你啊。
最後,初始化一下整部電影的英語劇名,也許有利於我們理解《重庆森林》(距本文寫作時已有10年)和王家衛本人何以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王家衛出眾地表現了“綿延”——極速閃過的時間、充滿活力的運動、時間的推移和延續,以及沒有盡頭的時間。雖然金城武用一大堆將要到期的鳳梨罐頭為他和阿May的緋聞畫上句點,而林青霞手上的一聽沙丁魚罐頭上的有效日期則是她填補失誤的最後期限,但這兒的時間並並非非常有限的,毋寧說是物質性的和可感的,即使王家衛讓時間具象化了:鳳梨罐頭、香皂、溼漉漉的破抹布、襯衣、毛絨填充玩偶、玩偶直升機。和普魯斯特的“小瑪德萊娜”一樣,那些時間的載體將主角送至對過去的記憶中。又或是,它們同村上春樹的科幻短篇小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中的那具骨頭一樣。金城武和郭富城對著那些攜帶著時間記憶的粒子說話,類似於村上春樹短篇小說裡的“讀夢人”對著骨頭說夢(因而也是“閱讀”延續的時間)。
王家衛是當下最有世界聲望的華語編劇之一。
王家衛難以專注於《东邪西毒》的創作,在攝製過程中,他不得不協調大明星們互相武裝衝突的檔期,還要參予創作一部由搭擋劉鎮偉主演的影片——《东成西就》(王家衛掛名聯合導演)。王家衛手上的另一部影片也延緩了《东邪西毒》的儘快開拍,這就是《重庆森林》。傳奇之處在於,王家衛藉助剪接《东邪西毒》的間隙,用了不到三個月就拍成電影了該片。王家衛將《重庆森林》描繪成一部由才剛從電影學院大學畢業的小學生攝製的經典作品:採用最簡單的電子設備,只用光線,以相似記錄片的條件攝製的一部廉價影片。影片的財政預算為1500萬港元,王家衛特別強調,在為三部大筆效率的影片殫精竭慮之後,攝製《重庆森林》好似讓他返回了年長時代。
王家衛在影之傑子公司的搭擋劉鎮偉是一名暢銷的商業片編劇,擅於攝製快節奏的喜劇電影和驚悚片,特別是在執導了大獲成功的《赌圣》(1990,劉德華主演)之後,劉鎮偉當時在澳門影壇的話語權略遜王家衛。便是在劉鎮偉的支持和幫助下,王家衛離開了影之傑,並創辦了他們的製片子公司——澤東電影有限子公司。他旋即著手籌備下一部影片,並再度對一部短篇小說進行翻拍,此次是一部經典武俠短篇小說——武俠小說的《射雕英雄传》。在新功夫片大潮達至顛峰的1992年,王家衛著手攝製整部定名為《东邪西毒》的影片。
“綿延”還彰顯在電影的音軌上。王家衛對外國音樂創作的感官擴展到他對流行曲的選擇上:“爸爸媽媽”樂團(The Mamas and the Papas)的《加州梦》(‘California Dreamin’)、黛娜·哥倫比亞特區(Dinah Washington)的《一日之别》(‘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丹尼爾·史密斯(Dennis Brown)具備雷鬼樂節奏的《生命中的事物》(‘Things in Life’)等。同樣關鍵的還有兩處寶萊塢味道的音軌,和晚上電視節目播映的京劇戲曲片。那些兼收幷蓄的音軌做為一種凌駕於空間之上的時間類型而發揮作用。
電影對“綿延”——由心理脈動和記憶所決定的時間和空間偶合(spatial articulations)——的最佳表達是第一段故事情節的開場章節中召喚了巧遇母題的一剎那:何志武在“晚上特快”點餐時,與張學友的配角(似乎又是一個“100%完美的男孩”)撞到一同,音軌是何志武的敘述:“我跟她最接近的這時候,我們之間的相距只有0.01釐米。我對她一無所知。五個鐘頭之後,她討厭了除此之外一個女人。”當《加州梦》忽然響起時,畫面淡出,接著淡入為郭富城出演的巡警在巡邏名單上簽字。他快步朝攝像機走來,摘掉禮帽,點了一份大廚沙拉。攝影機切至張學友,她身穿一件吊帶的白色T恤。《加州梦》在高聲動態播出。那場戲出現在動態,和著曲目的節奏而沒有轉換,兩人的對話如下:
在下文中,我將嘗試證明《重庆森林》是怎樣通過王家衛對時空偶合的編排而成為後現代主義電影實踐的樣板的。我們也許能從劇名講起,“Chungking”是空間,“Express”是時間。“Chungking Express”是一個均質化的暗喻,將三個互不兼容的概念取得聯繫在一同。影片中的空間,是由武漢大樓幽閉的環境所象徵的內部世界,而時間則是一個由鐘錶所表徵的接近抽象化的外部世界,但它是通過罐頭上的過期日和畫在餐巾上的假登機牌實現的。
(張學友點點頭,皮膚隨著音樂創作的節拍左右轉動。)
原作者 | [馬來]張長興
王家衛的經典獨白,反映了村上春樹短篇小說的對話藝術風格
郭富城對著幾塊香皂訴說心聲,張學友溜進郭富城的別墅,到處挪動東西,以此滿足自己的情感,金城武面對的則是一瓶鳳梨罐頭。他們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其它東西上。惟有林青霞的配角沒有情感。她不停地公益活動,活下來對她來說更重要。她就像一隻在武漢森林裡如入無人之境的惡魔。
張學友:對啊,吵一點挺好。不必想那么多事啊。
電影的主要人物是三個警員(金城武、郭富城飾)、一個戴著藍色假髮的神祕男子(林青霞飾),以及三個乖僻的男子(張學友出演的餐廳營業員和周嘉玲出演的空中小姐)。這些人物概述更讓人想到相同的類別:動作片、白色柯南推理片(由金城武和林青霞執導的第一個故事情節中的許多章節)、戲劇和劇情片(由郭富城和張學友執導的第三個故事情節中的許多章節)。王家衛更喜歡把這三個故事情節都稱作“獨身的愛情故事情節”(single love stories),那些生活在這座衛星城中的人具備共同的特點,即難以把他們的情感傳遞給適宜的對象:
《重庆森林》中的沙拉數目為數眾多,承擔著王家衛記憶的一個機能,關連著林青霞的歌手在場(在第一段中,則是與張學友取得聯繫在一同,她的在場同樣是歌手式的,但未有神祕色彩,即使她比林青霞或王家衛要年長得多)。但沙拉也是飢餓的象徵——由對愛的渴望而生髮出來的飢餓,這一主題好似是對《阿飞正传》的重演:該處,與其說是得不到投資回報的真愛,不如說是早已喪失的真愛。
另兩條將《重庆森林》與《阿飞正传》取得聯繫在一同的線索是雙聯畫式的內部結構。很惋惜,王家衛沒能拍成電影《阿飞正传》下集,但《重庆森林》完美地呈現出了三個愛情故事情節的雙聯畫。在那個象徵意義上說,整部影片以其自身的成就,可說是王家衛進行實驗的豐碩成果,而這恰是他在《阿飞正传》中沒能順利完成的。在攝製《重庆森林》的過程中,王家衛曾說他想“嘗試在一部影片中攝製三個互相交叉的故事情節”,並讓敘事的經濟發展“相似一部高速公路片”。
編輯|宜蘭
那些曲目地運用抵達了下列目地:撕裂我們對銅鑼灣或“晚上特快”在空間認知上的感覺。當我們聽見《加州梦》《一日之别》,和丹尼爾·史密斯淺吟低唱《生命中的事物》的前兩句歌曲(“每兩天都有相同的際遇,這一切都變化無常”)時,首先深感的是一絲錯亂,接著才訂下神來看見與某個某一曲目相取得聯繫的空間(《加州梦》與“晚上特快”、《生命中的事物》與夜總會場景外景地“Bottoms Up”夜總會,等等)。
張學友衣著的變化,正與時間相適應。在先導場景中,她身穿白色T恤;在後續場景中,她身著薄荷綠的外套。在郭富城與張學友的一連串“晚上特快”對手戲中,至少還有三次由衣著變化所指示的時間變化。該處,王家衛嗎做到了在時空中開拓村上春樹關於巧遇式的人物關係和記憶所飾演的配角的概念。能做到這一點的影片編劇,也許只有王家衛。帶白色心形花紋的白T恤,以及帶斑點的白T恤,指示了除此之外三次時間變化。
電影的國際版對澳門空間的表現極具抽象化意味。對外國觀眾們來說,武漢大樓、銅鑼灣和尖沙咀也許但咫尺之遙。銅鑼灣和尖沙咀被維港所隔開,對老澳門人來說,兩者之間的相距不言自明。澳門版有這種一場戲,即何志武跑向天星小輪並渡海,與此同時我們聽見他的獨白,是關於他買回的30聽將要在5月1日過期的鳳梨罐頭(“假如她不回去,我們的真愛將會過期”)。國際版對這場戲的刪掉(這段獨白被移到何志武在超市裡買鳳梨的那場戲),加強了劇中的空間是一個完整街區的幻覺:“武漢森林”是一個堅實的地理座標。但,由那些曲目在心理層面上所指示的“綿延”的其本質,促進觀眾們以別的形式觀看和思索。
《重庆森林》是王家衛第一部贏得國際發售的影片,本片迷倒了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前者的子公司“Rolling Thunder”買斷了國際發售權。國際版更長,涵蓋更多場景,比如林青霞在武漢大樓與一大群菲律賓人進行毒品交易的章節,伴隨著典型寶萊塢曲目的音軌,和極有可能來自某部寶萊塢電影的對話片段。沒多久,在林青霞遭到背棄之後,還有一個拓展的場景:她殺害了一個小男孩,向前者的母親追問這些潛在的毒梟的行蹤。國際版還對澳門版的兩處場景進行了重新排序或調整。
未來派音樂家嘗試讓靜止的畫布動起來。在某種程度上,杜可風和劉偉強重回靜止的畫布,好似讓影片迴歸其本源,將“運動-圖像”降到德勒茲所言的“特權性瞬間”(privileged instants)或“快照”(snapshots),以重新想像力量感。低速快門(slow-shutter-speed)攝影和“偷格加印”製造出粒子在運動過程或一連串定格靜態攝影機中的復現感(閃光的慢動作效果在《旺角卡门》中獲得出眾的運用,回想起來,那個王家衛的招牌效果真的是本片攝影師劉偉強的傑作)。那個畫法令運動扭曲,製造出虛幻的速度感,卻又弔詭地起到了靈動快速的效果。
張學友:你呢?
1910年的宣言是一則方法論歷史文獻。它一結尾就正式宣佈一種不斷增長的對於真理的要求,此種要求無法再滿足於以往所理解的那種方式和美感:一切事物都是運動的和奔跑的,快速變化的,此種天地萬物的運動,才是音樂家所必須力求表現的。空間不再存有,或是僅僅做為一種氛圍,粒子在其中運動著和相互穿插著。
《重庆森林》中何志武在一間夜總會碰上長髮男子。
王家衛經濟發展出一套關於虛幻的人物關係的主題,恰如《在一个美妙的四月春晨,遇见100%完美女孩》所呈現出的,此種關係轉瞬即逝。人物的生活只是出現輕微的接觸,但絕不會互相滲透(也許自己連接觸都談不上,只是失之交臂)。
何志武最終在一間夜總會碰上這個長髮男子,但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之後遇見過。自己開始攀談(這個男子頗不甘心),最後走進飯店的臥室。但此次遇見的變化卻出乎意料:她倒在床邊昏昏睡去,而他則一邊看著晚上電視節目播映的京劇戲曲片,一邊大啖大廚沙拉和炸薯條。
摘編 | 徐悅東
郭富城:你不討厭想事情?
《重庆森林》中幾段主角的巧遇同框。
王家衛電影中的這些皮膚運動、觸摸,又分離,而非“相互交織”。通過對除此之外一個男人出現興趣,金城武和郭富城的配角分別從失戀中恢復。但,在郭富城和張學友的例子中,此種興趣與否會進一步經濟發展,尚難下結論(影片結局——張學友看著郭富城翻修“晚上特快”——即使與王家衛的其它影片一樣曖昧,卻或許更多些希望);而金城武的例子似乎並非如此(至少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種的)。
在本劇中,王家衛想要表達的或許是,真愛是短暫的。這也是王家衛的本作《阿飞正传》的主題,其實它在《重庆森林》中的表達更為輕鬆:劇中的三個警員對待被婉拒的反應,從某種病態經濟發展到不在意,從失望經濟發展到聳聳肩,一笑而過。金城武“57個半小時之後再度愛上一個男人”;郭富城看見前男友趴在自己的三輪車上,報以笑容,並祝她美好。張學友的配角以其舞姿和荒謬的怪異行為加強了此種輕鬆的氣氛,輔之以高聲播出的《加州梦》和張學友本人獻唱的《梦中人》[演唱自“小紅莓”樂團 (the Cranberries)的《梦》(‘Dreams’)],這兩首曲目本身便須要搖擺皮膚、點頭頷首、用腳打拍子。當張學友輕舞並且幻想著加利福尼亞州的這時候,我們也想重新加入她的行列。
《阿飞正传》的電影票房慘敗對影之傑製作股份有限公司來說無異於一場大災難,王家衛也因而大受挫折,最終失去了攝製《阿飞正传》下集的機會。雖然王家衛的影片仍未取得商業成功,但他所創建的威望和人脈關係已經相當可觀。他不但贏得了當仁不讓的新晉編劇之名,但是收穫了這種精神上的堅韌(雖然他的羞怯、平和從其主演的影片之中便可略知一二),他有能力快速從《阿飞正传》未盡全功(換句話說至多順利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挫敗中振作起來。
文章標簽 一日之別 在一個美妙的四月春晨,遇見100%完美女孩 電影實踐理論 王家衛的電影世界 下樓梯的裸女 1963/1982年的伊帕內瑪姑娘 東邪西毒 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 加州夢 夢 伊帕內瑪姑娘 賭聖 夢中人 東成西就 阿飛正傳 生命中的事物 旺角卡門 射鵰英雄傳 重慶森林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